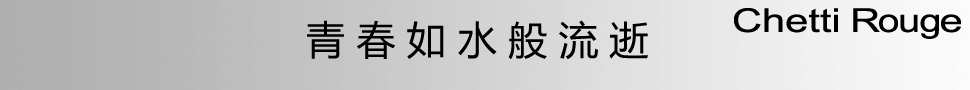埃利奥特同提伯说:「我曾经用了25年的时间接受了许多不同媒体的电视广播等采访,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同性恋者通过这个音乐节推动了世界的变化发
在音乐节之前,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很冷淡。他一生为了繁重的生活和照顾母亲而劳碌奔波,极少感到快乐。但在办音乐节的时候,他第一次拥抱了我。我终于在34岁的时候找到了爱我的父亲。尽管这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动力,却成为了我人生故事中重要的一部分。 「1969年夏天把破败丶粗陋的二号小屋变成了一座爱的宫殿。但是在我胡作非为的性爱的间隙,其他更微妙的事情也在发生,并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突然涌来的生意,我的周围尽是这些工人──年轻人,跟我以前接触过的非常不一样。有时候最简单的谈话也让人惊奇,首先,我发现许多到伍德斯托克来的人拥有梦想,那是任何普通纽约人想也想不到的,不论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 「稍后,州和地方官员将把雅思各农场里的人数估计为五十万。他们说一百万人还在路上,但困在了交通阻塞中,车辆一直堵到大约九十英里外的乔治华盛顿大桥。但是我相信这些估计是极其保守的。这远远多于时报广场任何一次新年夜的人群,而后者通常宣称有近百万之众。」 「这破败的三等汽车旅馆成了宇宙的中心。在我心底,我意识到,把布朗克斯丶布鲁克林和长岛来的头发乱蓬蓬的长舌妇换成这些色彩斑斓丶又辣又酷的嬉皮士,是要让我重生一次了。一生中第一次,我感觉人们理解我了。他们看到了我是谁。他们知道了地下影院是什么;他们欣赏长舌妇煎饼屋菜单上的庸俗艺术;他们与获得理解的感觉联系起来了。这是些关心环境和所有少数民族裔民权的人。这些人热爱音乐丶艺术和温顺的动物。看得出来他们拥有渴望,超越了仅仅追求成功和赚钱。我被此刻包围着我的这一族灵魂激励着。」──摘自《制造伍德斯托克》  《城市画报》:有人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像一场「梦」,因此它是无法重现再造的。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人曾经努力尝试创造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有更多人尝试重现音乐节。我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世界变了,要重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希望有人能证明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城市画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它使我找到了自尊,懂得自豪,懂得爱护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经常为工作和生活而感到沮丧忧郁。音乐节让我获得了重生,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不同的电视节目丶书籍丶戏剧和电影。勇敢去做以前一直梦想却不敢做的事情。《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到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幽默作家。当我因由我的首部小说《高街》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街》(Rue Haute)重回纽约冲击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关于伍德斯托克的书籍,在阅读之后,我发觉它们所说的不尽准确,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那时是1976年。我终于意识到音乐节是如此的重要。 「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和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橘黄丶粉红丶红丶绿丶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丶脖子上丶手腕和脚踩上都戴着珠链丶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丶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倦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我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责任拴在父母身上, 眼看着我挣的每一块钱被一个吸钱陷阱吞噬,这些都往我的内心慢慢灌输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永不消逝的孤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到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丶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城市画报》:有人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像一场「梦」,因此它是无法重现再造的。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人曾经努力尝试创造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有更多人尝试重现音乐节。我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世界变了,要重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希望有人能证明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城市画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它使我找到了自尊,懂得自豪,懂得爱护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经常为工作和生活而感到沮丧忧郁。音乐节让我获得了重生,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不同的电视节目丶书籍丶戏剧和电影。勇敢去做以前一直梦想却不敢做的事情。《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到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幽默作家。当我因由我的首部小说《高街》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街》(Rue Haute)重回纽约冲击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关于伍德斯托克的书籍,在阅读之后,我发觉它们所说的不尽准确,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那时是1976年。我终于意识到音乐节是如此的重要。 「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和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橘黄丶粉红丶红丶绿丶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丶脖子上丶手腕和脚踩上都戴着珠链丶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丶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倦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我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责任拴在父母身上, 眼看着我挣的每一块钱被一个吸钱陷阱吞噬,这些都往我的内心慢慢灌输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永不消逝的孤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到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丶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城市画报》:有人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像一场「梦」,因此它是无法重现再造的。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人曾经努力尝试创造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有更多人尝试重现音乐节。我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世界变了,要重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希望有人能证明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城市画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它使我找到了自尊,懂得自豪,懂得爱护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经常为工作和生活而感到沮丧忧郁。音乐节让我获得了重生,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不同的电视节目丶书籍丶戏剧和电影。勇敢去做以前一直梦想却不敢做的事情。《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到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幽默作家。当我因由我的首部小说《高街》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街》(Rue Haute)重回纽约冲击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关于伍德斯托克的书籍,在阅读之后,我发觉它们所说的不尽准确,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那时是1976年。我终于意识到音乐节是如此的重要。 「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和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橘黄丶粉红丶红丶绿丶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丶脖子上丶手腕和脚踩上都戴着珠链丶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丶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倦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我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责任拴在父母身上, 眼看着我挣的每一块钱被一个吸钱陷阱吞噬,这些都往我的内心慢慢灌输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永不消逝的孤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到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丶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
《城市画报》:有人说,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像一场「梦」,因此它是无法重现再造的。到目前为止,有许多人曾经努力尝试创造出另一个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但都以失败告终。今年有更多人尝试重现音乐节。我想,现在新一代的年轻人需要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伍德斯托克」,以此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受。世界变了,要重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也希望有人能证明我这个观点是错误的。 《城市画报》: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给你带来了怎么样的变化?它使我找到了自尊,懂得自豪,懂得爱护不同种族的人们。在此之前,我经常为工作和生活而感到沮丧忧郁。音乐节让我获得了重生,让我成为了一名作家,创作不同的电视节目丶书籍丶戏剧和电影。勇敢去做以前一直梦想却不敢做的事情。《城市画报》:你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1969年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不再仅仅是一场音乐盛会?有三年的时间,我移居到了布鲁塞尔和比利时,成为一名作家,一名幽默作家。当我因由我的首部小说《高街》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高街》(Rue Haute)重回纽约冲击奥斯卡奖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关于伍德斯托克的书籍,在阅读之后,我发觉它们所说的不尽准确,于是,我萌生了写一本回忆录的念头,那时是1976年。我终于意识到音乐节是如此的重要。 「这些人不是我一生中惯于与之打交道的纽约人。他们不是物质主义者,并不渴求财富和名望。他们是无法定义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拒绝了一切可算作通往那个称作美国梦的巨大幻觉的途径的东西。他们蓄着长发,穿着工装裤,屁股垮垮的,赤着脚,戴着方头巾,随性而为。很多人把头发染成了橘黄丶粉红丶红丶绿丶紫及蓝色。他们许多人头上丶脖子上丶手腕和脚踩上都戴着珠链丶和平标志和各种其他装饰品。有的人胡子蓬乱,极少有人按任何规律洗澡,而更少有人在意世界对他的认同。似乎每个人都在唱着丶笑着。我一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么多笑声。」 「到音乐结束的时候,我疲倦极了,无论身体上还是心理上,但却是绝对的兴高采烈。我第一次知道,我并不孤独。多年来,我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为责任拴在父母身上, 眼看着我挣的每一块钱被一个吸钱陷阱吞噬,这些都往我的内心慢慢灌输了一种深沉的孤独感──一种永不消逝的孤单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到我属于一个更大的群体,这是一个世代,它能通过其包容的态度丶极为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及其对这个摇滚时代的爱来自我定义。相关阅读:
- 无相关信息
专访特写
- 1专访《仔仔一堂》主持人Vinci:我不反对开放关系
- 2找一个GV明星当老公是什么体验?
- 3专访武汉网红1哥:参加健身比赛下体要塞护具!
- 4内裤男模Nick Masc参加上流男同志真人秀
- 5一个小城电视台的gay主持人
- 6同志演员Colton Haynes大爆好莱坞黑暗面
- 7精灵王子李·佩斯与男友结婚:我活着,我一直都是
- 816年坚守!北漂青年与他的防艾人生
- 9安迪·沃霍的性感男孩Joe Dallesandro
- 10同志摔角手Jake Atlas出柜后的心理折磨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