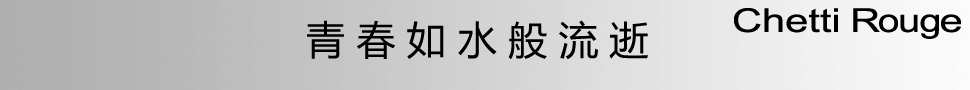埃利奥特同提伯说:「我曾经用了25年的时间接受了许多不同媒体的电视广播等采访,发现他们从来没有提及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同性恋者通过这个音乐节推动了世界的变化发
我是在1980年代才在纽约看到迈克尔·沃德利拍摄的纪录片《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疯狂实录》的。我当时对伍德斯托克简直是一无所知,我只知道这个音乐节很重要,有无数的人在赞美它。直到我准备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我才具体了解到音乐节的一些内幕。 说《制造伍德斯托克》从《冰风暴》之后我拍了6部都是比较重的东西,尤其到了《色·戒》,我感觉拍类似的沉重题材应该是到头了吧,很需要一些新鲜丶喜感与纯真,正好就碰到这个。 当时,我在三藩市Mill Vall的电影节宣传《色·戒》,《制造伍德斯托克》的作者埃利奥特·提伯就坐在我的后边,跟我讲了很多他书里边的东西,他讲述的过程很幽默很好玩,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月之后就拍了。《冰风暴》是在讲述伍德斯托克音乐节酒后宿醉的现象,我决定拍这部影片的时候正好碰到它的源头。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不断变换题材,是偶然还是必然?说老实话,我真的没有去吊大家的胃口,拍完一个故事之后总有另外一个故事去吸引我。如果不是这个故事这个电影,但在别的电影里也会讲同样的主题。 相关的时代精神的氛围也是吸引我的原因,我每次选的年代总是在很关键的结点上,我很喜欢戏剧点的东西,在转折点上的东西,特别发人深省。《冰风暴》和《与魔鬼共骑》中都隐含着对美国来说很重要的年份,但之前不太会有人注意。我注意到很多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年份,在此之前的前五年或者十年去想像,让他与当下的状况产生联系与呼应。 影片里其实并不是很多音乐会的镜头,只是有一些,而且还是远远拍摄的一些。这么做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资金的限制,更大程度上是因为艺术上的考虑。我想拍摄的是一部能把伍德斯托克音乐节埋藏到观众内心的电影,而不是拍一部以音乐会为重点的电影。而且我还想为这个音乐节保存一点神秘性,这个东西一 旦说透了丶拍出来了,它的意义也就丧失殆尽。 我克制不住要用这种纪录片式的片段,我拿了16mm摄像机,找了几个很有嬉皮士范儿的年轻人,让他们在片场随便拍,然后我把这些镜头一起剪辑到电影里。其实本来这个部分我想用资料片段剪辑,当我看到这些片段后,我想这就是我想要的老纪录片的感觉。这些镜头在影片里看拍得非常流畅,我们很开心,这些片段也反映了影片自由的主题,他们拍得轻松随意,连演员也包含在画面里,是非常风格化的部分。 我不觉得《制造伍德斯托克》会被看做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它和《断背山》不同。《断背山》讲的就是两个同性恋的故事,但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个音乐节的创办过程,讲的是一个关于「爱与和平」的故事。我们的主角是这个音乐节的创办人,这个创办人碰巧是埃利奥特·提伯,而埃利奥特·提伯碰巧又是个同性恋,仅此而已。我们没有在这上面做什么文章。 我很享受拍摄时被纯真的精神包围。很多人认为60年代就是嬉皮士年代,但嬉皮士只是很小的一部分人群,电影里展示的是各种文化现象,嬉皮士只是文化现象里的一部分,去往「伍德斯托克音乐节」路上的人,并不是个个披头散发,99%的人都是行为正常的,那些孩子只是想去现场狂欢。我不是一个向往嬉皮士生活的人,拍摄的过程让我回到了那个时代,沉浸在和平的气氛里,我很喜欢那个过程。「伍德斯托克」意味着和人平等丶和平地相处,和大自然保持平衡,对我来说,摇滚乐丶性和毒品只存在于「伍德斯托克」精神的边缘。「伍德斯托克」精神是和平,只有Abby Hoffman在舞台上砸吉他算是整个音乐节唯一暴力的场面。我并不是一个摇滚乐的粉丝,这是我理解的一个方向。 (本文根据李安接受各媒体的采访口述整理,未经本人勘校。) 本文原载:《城市画报》第236期2009年7月28日版
相关阅读:
- 无相关信息
专访特写
- 1濞戞挻鎹侀鏍Υ婵犱胶鍗氬ù鐘虫煣缁旀挳宕奸崒妯峰亾鐎b晛鐦滈柟闀愭濮瑰inci闁挎稒纰嶉崹婊勭▔瀹ュ懎鍐€閻庣數鎳撶槐鎴﹀绩閹冨綘缂侇垽鎷�
- 2闁归潧褰炵粩瀛樼▔閻欘毤闁哄嫬瀛╁Σ锕併亹閹惧厜鍋撴担绋垮絾闁哄嫷鍨划鍫熺▕閸粎绉煎Δ鐘茬焿缁憋拷
- 3濞戞挻鎹侀鏍ь潰閿旂晫婧勭紓鍐╁灩鐎涳拷1闁告縿鍎荤槐浼村矗閸屾艾顫i柛瀣ㄥ劥闂娾晛袙閺冨洨顩卞☉鎾愁儎缂嶅鎲版担鍓叉暁闁硅翰鍊曢崣鍧楁晬閿燂拷
- 4闁告劕鎳撻敓銉╂偨闁垮瑔涓痠ck Masc闁告瑥鍊告慨鐐寸▔婵犲啰銈﹂柣銏犲槻閹捁绠涘Δ鍐╁焸濞存粏娅i~锟�
- 5濞戞挴鍋撳☉鎿冧簻閻剟宕烘惔锝嗘毄閻熸瑥妫楄ぐ鎾儍閸掝湩y濞戞挾绮€垫梹绂嶉敓锟�
- 6闁告艾鑻换鏂库炕閺傛寧鍠匔olton Haynes濠㈠爢鍛€诲┑鍌氣偓鐔风疄闁秆呭仱缁箓寮冲Δ鍛〃
- 7缂侇喖澧芥导鎺楁偝鐎n亞鎽嶉柡澶婄瘈閾氬倸鍏婇柡鍌ゅ灟缁楀矂鎮藉畡鏉垮嚑缂備焦鎸搁…鐑芥晬濮橆厼鐏夋繛鑼跺吹濞煎啴鏁嶇仦鎯х亯濞戞挴鍋撻柣鈺傛尦閸忔﹢寮伴敓锟�
- 816妤犵偞娼欏ḿ銉р偓鐟扮墳缁辨帡宕犲Δ浣虹=闂傚牊甯掗崟鐐▔鎼存繄閾傞柣銊ュ濡插鎳濋崣銉︾溄闁活澁鎷�
- 9閻庣懓顦冲鈧捄顖氣柦閸愵喗绠涢柣銊ュ閳ь儸鍕Τ闁汇垹鍢查顢皁e Dallesandro
- 10闁告艾鑻换鏃堝箺閺冨浂娼¢柟闈涒攰ake Atlas闁告垹鍎ら悡鏍触鎼达絾鐣遍煫鍥у暟閹﹪骞庡Ο纭风礄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