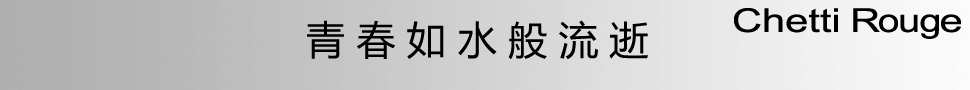对于有一群人,迪拜给予的突然自由和解放倒是真的,可是,这群人恰恰是政府最不想解放的。他们是同性恋者……来到这里几个月后我才意识到——一切都是假的。你所看到的一切。树木是假的,合同是假的,岛屿是假的,笑容是假的,连水都是假的……
阿赫穆德·阿尔阿塔是个23岁的英俊青年,留着修剪整齐的胡须,一身剪裁合体的白色长袍,戴方框眼镜。他说一口流利的美国英语,很快向我证明,他对伦敦、洛杉矶和巴黎的了解超过多数西方人。坐在星巴克咖啡店里,他宣布,“这个国家是年轻人的天堂!政府负担一切教育费用,从幼儿园一直到博士。结婚后可分到免费住房。还可享受免费医疗,如果这里的条件不够好,政府还出钱送你去外国治疗。不用交税,甚至连电话费也不用自己交。几乎家家都有佣人、保姆、司机。你难道不想成为阿联酋人吗?” 我试图反驳,但被他打断,“您看,我的祖父每天都得累死累活。要喝水,他先得去井里打水。井干了,他还得请人用骆驼从遥远的地方送来。他们那一辈人总是在挨饿,总在找活干。因为医疗条件不好,他一辈子瘸腿。现在看我们!”
对于阿联酋人,他们的国家像个童话国度。像多数本地人一样,阿赫穆德为政府工作,因此他们几乎不受经济危机的影响。“我没有感到什么影响,我的朋友们也一样,”他说,“我们的饭碗是保险的,除非干了十恶不赦的坏事,一般不会被解雇。”
当然,洪水一样涌入的外国人有时候确实像是“眼中刺”,阿赫穆德说,“但我们把他们看成发展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我们还能怎样?谁也不想回到沙漠过游牧民的生活。我们从像非洲一样贫困的国家,变成人均年收入12万美元的富国。有什么好抱怨的?”
他说他不介意缺少所谓的政治自由。“你会发现要找到一个不支持穆罕默德酋长的阿联酋人很难。”因为他们不敢说真话吗?“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支持他。他是一位伟大领导。你看看就知道!”他微笑说,“我相信我的生活和你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喝咖啡、看电影、和朋友聚会。不同的是,你在伦敦的星巴克,我在迪拜的。”说着,他又叫了一杯咖啡。
所有的阿联酋人都这样想吗?在时髦的迪拜塔酒店,我见到31岁的苏尔坦·阿尔卡塞米。他是迪拜通讯社的专栏作家兼艺术品收藏者,代表了少数的改革派。他穿着西式衣服——蓝色牛仔裤、拉尔夫劳伦衬衣——语速很快。“这里的人变成了懒惰的肥胖的大宝宝!”他抱怨说,“保姆国家制度走得太远。我什么都不干!我们为什么都不为私人公司工作?父母不能照看他们自己的孩子?”但当我提到迪拜的奴役现象时,他被激怒了:“做人应该公正,”他坚持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宽容的人。迪拜是唯一的真正国际城市。每个来到这里的人都得到尊重。”
我突然想到了Sonapur的劳工营。就在几英里之外。他不知道它们的存在吗?他很恼怒,“如果每年有三四十起虐待工人事件,听上去似乎很多,但请考虑到有多少人来到这里……”30?40?虐待像瘟疫一样泛滥。我说,我们谈论的是成千上万。
他勃然大怒,反驳说:“你认为墨西哥人在纽约的待遇就很好吗?你知道英国人花了多少时间才学会善待外国人?我可以去伦敦写那些街头流浪汉,你们的城市听上去也很可怕!那些工人随时可以离开!”
但他们不能。他们的护照被扣留,工资被扣发。“对此,我很抱歉。那样干是违法的,应该受到惩罚。但他们的大使馆应该伸出援手。”他们尝试过。还有,你们为什么禁止工人罢工。“感谢上帝,我们不允许那样干!”他大声说,“罢工太不方便。我们不像法国,整天闹罢工。请想象假如一个国家的工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停止工作!”那么,工人如果上当受骗,他们该如何反抗。“离开这个国家。”
我叹气。苏尔坦情绪沸腾。“西方人总是在抱怨。”他说,“你们为什么不善待动物?为什么你们的香波广告如此可笑?为什么不对工人好一点儿?”这个排序让人深受启发:动物,香波然后才是工人。他激动地在椅子上动来动去,指着我说,“我给我的工人戴护目镜穿防护靴,他们还不要!说这妨碍他们工作!”
- 无相关信息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