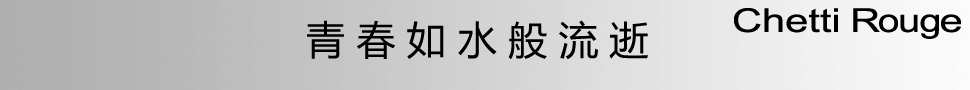维兰德同施佩克在谈电影、谈同性恋么?其实他一直谈的都是政治
刚才有人把同性恋和政治这两个概念割裂开来,这是非常有问题的理
那是第一届泰迪熊奖评奖的夜晚,又寒碜又美好。 《柏林墙以东》在各大电影节上频频获奖,施佩克体会到了奖项对于一个电影导演的支持有多么巨大。1987年,施佩克和他的伙伴Manfred Salzgeber决定创办一个针对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议题的电影奖项,也就是泰迪熊奖。 阿尔默多瓦的《欲望的法则》获得了奖。没有颁奖礼,没有红地毯,甚至没有奖杯,他得到的奖励是一张印有泰迪熊的小卡片。施佩克把它塞进了信封里,寄给了阿尔默多瓦。这对阿尔默多瓦来说,已经是惊喜,他甚至没想到自己能获奖。 第二年,泰迪熊奖终于有了个庆祝仪式,但只是在同性恋中心举行,只有250人参加,这和今年3000人的颁奖晚会相比,完全不值一提。1992年,泰迪熊奖正式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官方奖项,确立了同性恋电影在主流影坛上的地位。 自1987年创办25年来,泰迪熊奖奖掖了阿尔默多瓦(Pedro Almodovar)、德里克·贾曼 (Derek Jarman)等众多杰出的导演,其中不乏中国导演的身影。1998年香港导演关锦鹏的《愈快乐愈堕落》,获得“泰迪熊最佳剧情长片奖”,在关锦鹏擒获那个奖项的十多天前,他借助那个片子于香港出柜(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 施佩克逐渐开始认识到,应该走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奖项。每个人都可能有个gay叔叔,gay朋友,毕竟同性恋人群占到柏林人口比例的10%,这让异性恋群体能更多地接触到同性恋群体。 而现在,对大多数柏林人来说,Schwul 不再是一个贬义词,只是一个中性的词语。 Q&A 南都周刊:在您负责的全景单元里,为什么会关注同性恋这个题材? 维兰德·施佩克:要给边缘人群一个表达的空间是很艰难的,刚一开始,这样一个空间是非常小的,要拓展成为一个机制化的表达空间就更有难度了。我们知道涉及一些边缘人群题材的电影都是很难发行的,这其中也包括了亚洲电影。我想给这类影片一个平台,在“全景”单元来呈现这一类电影,使它们能够有空间表达,甚至获得发行的机会。当这些影片的预算捉襟见肘时,可以通过非常巧妙的设计和操作,得以拍摄并且获得足够的观众。但也正是因为有这类题材,才使“全景”单元具有相当的特色。 南都周刊:您为同性恋和跨性别题材创立了一个电影奖项─泰迪熊奖,为什么要叫泰迪熊奖? 维兰德·施佩克:这和美国同性恋运动史有关。 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末期,美国第一代的同性恋运动者们希望通过一种方式,让别人知道他们是同性恋。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让泰迪熊成为每个人佩戴的一个物品。大家在背包上挂上一个泰迪熊,用这种方法让其他同性恋群体的人知道,他们并不孤独。泰迪熊在那一轮浪潮里起到了独特的作用。另外一个原因,每个人其实都和泰迪熊有种亲近感,它是在床上除了自己身体外,可以放置的另外的东西。而且,柏林市的吉祥物就是柏林熊。柏林电影节奖项也是金熊奖,泰迪熊是电影节这家族的一个成员。 南都周刊:你怎么看同性恋的自我身份认同和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 维兰德·施佩克:我想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自己是谁,这不是指性取向的同性恋,而是指意识到自己属于少数族群,这是一种政治意识。这使得我在公众场合来表达自己。当拍摄一部电影时,总是希望别人来看。它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样政治意识和艺术想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举个例子来讲,在中国大陆,可能因为有同性恋电影导演崔子恩的存在,对这个主题感兴趣的人才可能看到这类电影。很可能对另外一些人来说,会是他们第一次通过银幕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这其实就是我做这个项目的动机,甚至也是我做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的动机。 南都周刊:如果一个艺术家因为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只局限于同性恋题材的创作,会不会损害艺术品质?
相关阅读:
施佩克
- 无相关信息
专访特写
- 1涓撹銆婁粩浠斾竴鍫傘€嬩富鎸佷汉Vinci锛氭垜涓嶅弽瀵瑰紑鏀惧叧绯�
- 2鎵句竴涓狦V鏄庢槦褰撹€佸叕鏄粈涔堜綋楠岋紵
- 3涓撹姝︽眽缃戠孩1鍝ワ細鍙傚姞鍋ヨ韩姣旇禌涓嬩綋瑕佸鎶ゅ叿锛�
- 4鍐呰¥鐢锋āNick Masc鍙傚姞涓婃祦鐢峰悓蹇楃湡浜虹
- 5涓€涓皬鍩庣數瑙嗗彴鐨刧ay涓绘寔浜�
- 6鍚屽織婕斿憳Colton Haynes澶х垎濂借幈鍧為粦鏆楅潰
- 7绮剧伒鐜嬪瓙鏉幝蜂僵鏂笌鐢峰弸缁撳锛氭垜娲荤潃锛屾垜涓€鐩撮兘鏄�
- 816骞村潥瀹堬紒鍖楁紓闈掑勾涓庝粬鐨勯槻鑹句汉鐢�
- 9瀹夎开路娌冮湇鐨勬€ф劅鐢峰Joe Dallesandro
- 10鍚屽織鎽旇鎵婮ake Atlas鍑烘煖鍚庣殑蹇冪悊鎶樼(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