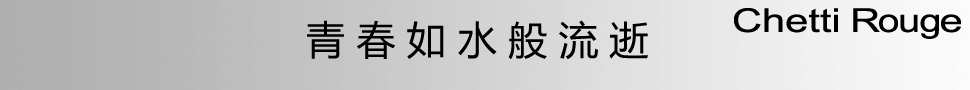我在书桌画作业,李察自动坐在床上,先是扯些一听就分辨得出更掰的话题,最后才硬生生问出口:“你们……你们也同样作男的跟女的那件事啊”
“你是说作爱是啊。”我决定以所能努力的最大方态度,应付来意不明的李察。
“那……你们谁是男的谁是女的你知道我的意思……”他的两眉微皱,双手比划了几招上下体位。
“我们都是男的,也可以都是女的,如果我没有误会你要问的话。”
“我无法想象两个男的作那事,原谅如果我说得太白了,同样是有洞没错,可就不是那个功能嘛。”李察的脸浮掠过一丝不经意的嫌恶。
“为何你们看同性恋者,总像只看他们在房里作什么,而都不是看见他们的为人。可是当你们在看异性恋者时,就很少会去想他们在房里作的事好象同性恋就是一种不雅作爱姿势的代名词,你们如果因此觉得恶心,也只能说是因为被自己脑中所想的,给搞反胃罢了。”
“那么,你们非得结婚不可吗你们又生不出小孩结婚可不是孩子们玩游戏,嘿嘿,外人搞不懂你们在干什么。”李察咳了数声,脸色微露轻蔑。
“生小孩,又不是人类结婚的唯一目的,假如你对婚姻的了解仅上于此的话,那我可能要说一句重话,我一点也不讶异你保不住自己的婚姻。”我凝视着他,硬生生接招,水来土掩他的敌意。
他像一只被踩到尾巴的猫,双瞳放出精光,脊梁拱起。我原想他会怒气发作,但半晌,他放垮了膨胀的双肩,说:“well,你说得没错,嘿,我是离婚了。”我几乎以为看走了眼,李察眼中的那支水桃花竟绽放了几瓣:“你……你会不会喜欢我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是说如果我也是的话。”
“你不会喜欢所有的女人吧同样道理,男同性恋者也不是没有选择性,只要是男的统统要。”
我睹见李察的表情,宛若一枝沾露欲滴的桃花,因搞错了季节,过早绽蕊,当场冻僵了。
我为同性恋社区中心绘的那几面壁上画,引起不少好评,爱德华特别向我说起有一家专门展出同性恋主题的画廊,有意和我联络。这即是我和“出路”画廊牵上线的原因,经理是三十许的派屈克,麦栗色长发扎成马尾,与路一般,眼睛是万里晴空的蓝,却无比深远。他问我有无现成的作品,一听说我在“大杯子”素描人物涂鸦成册,大感兴趣,看了更中意,似乎还用了一个“族谱”的字眼来形容,说这是最草根却最真实的同性恋族群的生命。
派屈克毕竟专业出身,对我的画喜爱,不像一般人用很中性的“噢,真迷人”、“哇,棒极了”等不痛不痒的词藻,他一针见血刺进了我的画穴。例如他一看见小淫球的速写,拍手大笑:“听朋友提起过那家咖啡店有只店宝,我虽没见过牠,却几乎从你的画感到这头鹦鹉呼之欲出,看牠像一个小孩,走进一家成人录像带店,望见花花绿绿的包装盒,然后回到家,在爷爷奶奶都在的家族聚餐上,突然冒出包装盒子上的广告词,香艳喷火,结果却让全家的大人喷饭。”
派屈克对嗜爱开黄腔的小淫球,形容得鞭辟入理,那天以后我只要起来,就在心底大笑。我因此常摊开小淫球的素描,确实越看越像一个语惊四座的黄看小孩,淫声秽语与无邢神情牛头不对马嘴,形成可笑对比。
阿官对我将在“出路”办画展亦感荣焉,也喜欢以“族谱”为画展名,以及将我举下那些千姿百态的同性恋者,称作我们的族人这个主意。我忽心念一动,翻开小淫球劲张素描问他感想,阿官是挺认真看了一会,答案却令我泄气,竟是那种我最怕的中性说法:“噢,你把那只坏女孩画得真迷人。”
我开始和派屈克联系频繁,修正展览细目,逐一敲定。当我们在挑画时,他好比是占星师,精谙读心术,屡屡一言中的,说出画里玄机,好的不保留,越的不隐瞒,让我忽而冒汗,忽而偷偷喜欢,我简直有赤裸裸站在他面前绦处藏躲的窘迫。
当画展排上档期后,派屈克要我补画几张大幅的炭笔速写,从这时起,他逐渐变化风格,全然公事公办的专业嘴脸,对我的画批评常如一帖帖重而猛的苦药,不再是过去的糖汁甜浆。他眼光之利,下评之犀,使我更加慌张。
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派屈克先用香饵将我骗上,就为了这样修理人他以前说的好听话越是画龙点睛,以同样的功力,他如今说的重话就只有越捅中要害的份。他说我在“大杯子”画得那票人物虽然随意,但有一种灵活灵现的气质,浑然天成;现在刻意去创作的炭画,却怎么也抓不到原来的那股生活精髓。派屈克不留情地说:“你那些素描就像在河床散步,无意中捡到的天然矿石,剖开里头有晶钻,现在你的画的呢,挺多是自己在家里加工打磨的玻璃珠。”
我陷进一片流沙似的焦虑,派屈克越挑剔,我就越不服气,但我画了几幅,他那句鱼目混珠的论调,始终下了蛊一般萦绕在脑海,越急便越画不出来。我疲于奔命,来回走在旧河床上,却什么也捡不到了。
当我在焦躁中沉沦,才发觉阿官一点也进不到我的绘画世界,他远远隔在外头,连门都找不着。阿官只能劝我别急,看着我撕掉的一张张灰画,他说:“我才不管那个派屈克怎么讲,我看挺好的嘛。”
我不仅焦急,隐约也害怕,因为体察到不知何时起,对派屈克有了异样心思。我每次找他谈画、看画,其实暗地情不自禁急着讨好他,不论是他评画的品味或更糟的是心灵的共振,都渴求能回到与我乍见之初的欢心,天我甚至以一种几近献身的仪式仰慕他。
那天,派屈克邀请晚餐,我第一次上他在苏荷区的家,亲睹了他的画作,当场惊吓。他的油画一派浓郁葱茂,活似一座座恐龙时期的原始丛林,木壮叶霸,花艳草野,神秘的史前生态重返人间。我豁然明白,可不是吗派屈克不就是一座谜样的林相远看近观俱不同,内在岚气飘浮,深不可知。
与他交往,像在浏览一道道谜题,我沉吟苦思,除非他自己现出谜底,否则我走不出迷宫。派屈克谜也似的气质,让我一寸寸往流沙深处陷。当餐后放映他的作品幻灯片,我不是没见过出色创作,但他的画有种古老自然界的蛊媚,弥漫着远在文明诞生之前的不可知氛围,看得我心口发颤、耳热、口焦、神经放电。
同志小说
- 古代同志小说:男妻男妾2023-04-24
- 中篇同志小说:10692022-01-03
- 古代同志小说:我是南山一少僧2021-12-26
- 真实悲剧同志小说:受伤的芦苇不开花2021-12-02
- 真实悲剧同志小说:受伤的芦苇不开花2021-12-02
- 已故同志小说作品:我等你到三十五岁2021-12-02
- 已故同志小说作品:我等你到三十五岁2021-12-02
- 1阿尔兹海默症的姥姥劝同志孙子离开家
- 2毁容的外卖小哥与他的新男友
- 3欧洲同志浴室游记
- 4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5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6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7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8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9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10你好,警官!
- 1曼谷警方突袭男同志“内裤派对” 现场缉获毒品 扣查97人
- 2Grindr年度大数据:约旦1多南非0多 美国人最爱换裸照
- 3曼谷咖啡馆39 hornet暗藏玄机?!楼上别有洞天即时发展!
- 4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5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6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7“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8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9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10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