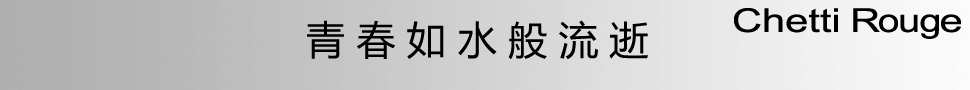K是双性恋,他的太太知道他是双性恋,但并不知道他有个BF。他们俩有一个5岁的孩子,现在上海上幼儿园。K现在在北京工作,基本上一个月回家1-2天。偶尔,他太太也会来北京看他。
今年7月,一条“艾滋病感染者信息泄露遇诈骗”的新闻迅速传播开来,闹得沸沸扬扬。在这场诈骗风波中,全国30省有275位艾滋感染者称接到了诈骗电话,对方谎称自己是政府部门或卫生局的工作人员,将给艾滋病患者发放补助,并要求患者提供手续费。一些诈骗分子则要求患者输入手机验证码,随后患者银行卡里的钱全部被转走。这些诈骗分子事先掌握了艾滋病患者的大量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户籍、确诊时间、就诊医院等。一时间,艾滋病患者的个人信息遭到了大面积的泄露。
K是双性恋,他的太太知道他是双性恋,但并不知道他有个BF。他们俩有一个5岁的孩子,现在上海上幼儿园。K现在在北京工作,基本上一个月回家1-2天。偶尔,他太太也会来北京看他。
K很晚才意识到自己是双性恋的事实。因为工作的原因,K经常在外出差,在上海待的时间很少。在外出差累了的时候,K会找人做按摩,但他不太想让小姐来做按摩,于是就找了男按摩师。恰巧一次,他住在酒店,直接通过酒店叫来了按摩师,而对方可能是MB,两人就发生了关系。K说,当时完了之后还感觉挺好的,想着这也不算出轨——当时的K,已经结婚6年,并且有了孩子。
在此之前,K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也喜欢同性的倾向。在与同性发生了一次关系后,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接触这个圈子。两三年之后,K在贴吧看到有人在谈论相关事情的时候,才开始真正接触到这个圈子。
有趣的是,K的BF,也是他在外地出差时,由圈子里的人介绍认识的。他们认识三四年了,但BF在江苏,K在北京,两人是异地恋,都已经结婚。最开始认识的时候两人经常在一起,现在则是大半年见一次,平时通过微信联系。
今年的5月份,K的公司组织了一次体检。K看到体检表里有一些内容可以自由选择,就选了输血八项。
结果出来了。K得了艾滋病,他脑子里一片空白。
K并不清楚自己是在哪次行为中感染的,“很有可能是在年初的时候吧。”
K之前了解过艾滋病的传染方式等一些较为表面的知识,但并不详细。确诊之后,K开始主动去搜索相关消息,并且实话告诉了家人自己是怎么得病的。
家人没有太惊讶,他们对这方面信息也有一些了解。“我算比较幸运吧,家里没什么变化,很快就接受了。”在家人的督促下,K开始吃药接受治疗。
BF知道了以后,也积极鼓励他。所幸的是,BF没事。
在经历了差不多一个多月的绝望与无助之后,6月中旬,K渐渐“不再去想这个事情了”,而现在,“可能我自己都快忘了”。K笑着说,“现在控制得挺好的。”
不过有的事情呢,不是你去找它,而是它主动上门来找你。
两个月后,7月10号那天,一个周日,K正在和家人吃饭。手机响了。
对方问:你是不是K本人?
K干脆地回答说:不是。
在此之前,K已经在白桦林群里得知不久前有类似诈骗的事情发生。
对方又问:那你是不是K的家人?
K回答:是。
对方接着问:K感染了艾滋病,你们家里人知不知道?
K反问道:你怎么知道K感染的事情?
对方回答:我是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K的病就是在我们这里检查出来的,现在在我们这里治疗。
不知是K的幸运,还是骗子太倒霉,K的病确实是在协和医院确诊的,但由于协和离他工作居住的地方太远,确诊之后他就到了地坛医院接受治疗。骗子一不小心,说漏了嘴。
之后,对方还给了K一个电话号码,让他联系。
K问:如果我们不打电话,会怎么样?
对方回答:那就把病人除名了,他就享受不到政府的政策优惠了。
K回答道:那你就除名吧。
没有多说,K就挂掉了电话。
K说,当时自己还是有一些阴影。他担心对方如果打电话到公司去,会发生什么问题。后来他打定主意,如果对方真这么做,他就矢口否认。他所在的公司既不是国企,也不是事业单位,没有权力要求他提供相关信息。而且根据国家规定,他完全可以让疾控中心出具没有感染的证明。不过转念一想:对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不太大。第一,在疾控中心的病单上,K没有提供自己的工作单位。在北京,这不是必需的。第二,即使对方可以根据他的手机号码进行搜查,但这样一来,对方的作案成本就变高了,对方应该没有必要这么做。
“想想看,大不了就换一份工作吧。有能力的话,还怕找不到工作吗?”
而直到现在,K也没有再遭到类似的诈骗骚扰。“除了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外,已经基本上没什么感觉了。”
对于艾滋病患者来说,信息泄露最大的问题,就是诈骗分子以此进行威胁、敲诈,或者直接联系患者的工作单位、亲朋好友,造成很大的麻烦。而像K这样向家人坦白自己病情的,在感染者中并不是太多。有的人得病之后,甚至瞒着家人,更别说让同事或者亲朋好友知道了。
K认为,从国家管理的角度讲,国家补助提供免费药物,医院作为发放药物的机构,需要知道有哪些人在使用药物。有些药物如替诺福韦酯(Tenofovir disoproxil fumarate,TDF)和拉米夫定(贺普丁,3TC),除了艾滋病之外,乙肝病也是需要这两种药治疗的,在乙肝病没有实行免费政策之前,曾出现过倒卖药物的情况。在管理上讲,还是需要提供个人信息。但另一方面,K觉得患者信息不应该被保存和收集起来,患者只需要在领药的时候提供信息就可以了。而患者信息被收集起来以后,又没有很好地保护。
K说,诈骗事件以后,他自己也很注重个人隐私的保护,能够少提供、不提供的信息尽量少提供、不提供。他还准备了两部手机,在填写病单时就用另外一个号码。
“感觉自己在自身条件上,比其他感染者来说,要有优势一些。”K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中充满了自信。
K说,生活中有很多人不太了解艾滋病感染的机制,以及药物的副作用、用药的注意事项等情况。即使是被感染了,可能会知道一些,但知道的也不多。有的人不知道该去哪里搜集信息,而网络上的信息真伪难辨,像吃中药能治愈艾滋的说法,就误导了很多人。实际上,如果我们了解到艾滋病的感染机制,就知道中药最多只是缓解症状而已。
K的BF对艾滋病了解较多,他告诉K可以去白桦林群里咨询一下。K在贴吧里找到了群号,在群友的分享中了解了一些信息,之后自己又去查了一些国外的文献,阅读了微博上专家分享的一些内容。
渐渐地,K对于病的了解愈多,他的恐惧也就愈少。
“因为你会比较清楚它可能会对你有些什么影响,特别是在病毒被有效控制住以后就没有什么了。”
K发现,因为目前对于艾滋病并没有治愈的药物和方法,加上前些年国家对于艾滋病的妖魔化宣传,导致大众的恐惧和歧视心理。国家的宣传一直都存在,但都停留在比较浅的层面。宣传最多的方面,一个是危害,一个是传播方式。而对于得到有效治疗后的情形,宣传很少。而公众能搜索到的信息,很多都是负面的。“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公众会从不可治愈性上歧视你,从道德上去批判你。他们会认为你就是乱搞才得了这个病。批判的人从道德上讲,不见得比别人高尚——这是人性的弱点。”
但实际上,乙肝和艾滋病的传播渠道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起初国家在宣传时并没有着意宣传乙肝的感染途径,很多人把乙肝和甲肝混为一谈,以为乙肝就是“吃”出来的,跟性行为没有关系。乙肝病人受到排挤,主要也是因为公众以为乙肝是“吃”出来的,忽略了国家的宣传,也很少有人去批判乙肝病人的私生活。但很少有人知道,乙肝也是可以通过性传播的。
目前,乙肝病已经可以实现功能性的治愈,社会公众对乙肝的恐惧也没有什么严重了,来自社会的歧视和压力也小了。但艾滋病患者却完全不是这个感觉。如果艾滋病患者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病情,会引发非常严重的后果。
对于K来说,感染艾滋对他个人的影响几乎是没有的。除了吃药之外,他的日常生活依旧如昨,忙工作、玩游戏、健身,保持着早睡早起的生活规律,更加注意饮食和作息。他和BF有过亲密行为,但BF对此也并不害怕。
K唯一担心的是,如果自己的病情让其他人知道了,可能会导致他人的歧视。“了解这个病的人非常非常少,感染者自己很多人都不懂。”
而对于有经济压力的感染者来说,类似的诈骗行为,就显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但对于K来讲的话,他无所谓了。
K的经济条件还算不错,得病后没有使用国家提供的免费药,而是自费替换了一部分副作用比较大的药物,每个月花费近2000元。3个月后复查,他的病毒载量检测只有40多。
对于经济不是很宽裕的患者来说,如果是服用国内的免费药,它带来的副作用是很大的。像依非韦伦(施多宁)具有神经毒性,会让患者头晕、多梦,还有可能产生抑郁。六七年前,依非韦伦在国外还是通用的一线药,但现在因为它的神经毒性,已经基本上被放弃。K自费替换了二线药利托那韦(Norvir,克力芝)。这是一种蛋白酶抑制剂,它的副作用主要在于增加血脂。但由于国内自费药的选择余地很少,而他又没有时间国外买药,所以其余两种药物也没法替换。
K说,艾滋病没有那么可怕,防范当然是必须的,但如果不幸感染了,也没有那么可怕。5年前,谁都不会想到现在能制造出这么多药,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副作用。目前的药物研发,都是朝着如何延缓病人的寿命、减少药物副作用、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去做的,并且正在朝着如何实现功能性治愈和最终治愈的方向努力。目前看来,基因疗法可能是一种比较有希望的疗法。
谈到对目前国内艾滋病防治的现状,K说,他有三个希望。
一是希望国家能够更多地引进国外的新药,替换一些副作用很大的药物。最近几年,关于艾滋病的治疗越来越多,在欧美很多药的成果已经面世并且投入使用,但在国内还没有那么快。而副作用较大的药物会产生头晕、多梦的症状,有些人吃了以后,只能坐着,什么也干不了。有些人的头晕症状甚至会持续到第二天下午,对于生活和工作产生很大的影响,无形中也会增加压力。
二是希望国家扩大免费药的范围。这对于经济状况不是很好的患者来说,是很有必要的。
三是希望更多地去宣传有效控制病毒以后的情况。如果绝大部分感染者对这方面有所了解的话,他们的生活状态会变得更好。K说,他不敢说让自己的寿命跟普通人一样,但至少活到60岁是没有什么问题。
“但60岁之后,这个病会不会被治愈,谁知道呢?”
K坦言,他对未来没有什么打算,跟BF之间也主要是精神上的联系。得病之后,他也不再去外面发生关系。他觉得,感染这个病对家人是一种伤害,如果再不回头,也有点辜负家人的期望。
K不会去想未来,因为未来实在是太远。目前公众对于艾滋病的了解越来越多,相关药物的研制也越来越多。“我想再过几十年,可能就可以治愈了。”
K在期待。
他期待着将来可以出现新的治愈方法。
“你想,如果有了治愈方法,但治疗费用很高的话,你怎么办?”
“与其担心未来的状况,还不如过好现在。”
我觉得,K面对艾滋病的态度,就是面对。了解之后,主动去应对问题,比消极面对要好很多。这样做不见得最后会帮助患者彻底治愈疾病,或者减少副作用,但对于生活质量的改善会有很大帮助。
“当你的生活慢慢充实起来以后,你就会慢慢忘掉这些东西。”
“但我可能比较特例,所以(诈骗事件对我的)影响很小。接到电话以后也想得很清楚。很多事情,其实你想通了也没什么。等它发生的时候再说吧。”
生活在花花世界,心态和生活经历,其实都很重要。
艾滋病感染者
- 自杀未死!艾滋病感染者W2016-07-23
- 艾滋病感染者教我的事:与HIV一起生活2013-09-03
- 一位男同性恋艾滋病感染者的真情自白2011-11-17
- 他走了 一对艾滋病感染者的生死孽情2009-04-03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