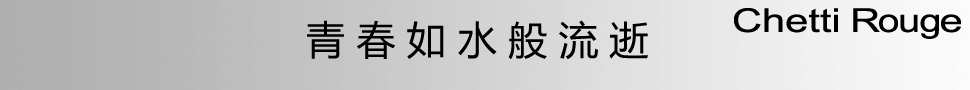在这座阴暗的发着霉味的木制老楼内,他拉合一碰便簌簌落尘的蓝旧棉布窗帘,把我摊在窄小的硬绑绑的单人床上,撕开我的衣裤,亲吻我一夜未曾冲洗的汗水干涸过的身体。
一
半年光阴很快过去,工作已经稳定,收入虽然不多,也足够日常开销。
我并非贪得无厌之人,每到周末临来,总有负罪感。每次去他那里都是一样的情形,我面无血色坐在皮沙发上,他嬉皮笑脸贴过来,搂着吻着,然后抱到房间去,他的一双肥胖黝黑的大手抚摸着我的身体,有种碎石粗砂掠过的疼痛,那感觉竟斧凿般深刻难忘。
一片黑丛丛的烂藻地里,生出一株即将枯败的野山菌,丑陋、矮小,黑红杂乱无次序地交替着,一圈深刻的疤痕环状地分割。上与下,十分鲜明。两只坟丘般的睾丸高低不平、大小不一,长满了黑草,闹轰轰地塞在烂藻地中,辨不清晰。野山菌被唤醒,瞬间壮大,却仍就矮墩可笑,僵在空中等风干。我也即将风干。
房间内有阴暗潮湿的霉味,昏黄台灯照在角落,一台液晶电视屏上,蓝光闪现,像一只只鬼魅的眼睛。
早上他还没起床,我已洗漱完毕,推醒他,说公司要身份证原件,先给我,用完再给你。他哼了半天,迷迷糊糊告诉我放在哪里,没有半点疑惑,我赶快把身份证收好,迅速离开。走时,摸到口袋里他每次半夜塞来的路费,倒也公平,一码归一码。
这一夜,睡得并不平静,四周仿佛有无数双诡异的小眼睛,窥视着我的过去,屈辱的过去。我侧身,不能入睡,月光渗进窗帘内,暗得心寒,不过天亮后,一切都将结束,都将被抹去。
没有跟他打招呼,第二天就开始搬家了,钥匙留给他的老邻居。不知道要和他说什么。我另外找了一个窄小的住处,很便宜,这回付得起。没有多余的钱置办家里的东西,拿走了那张小的单人床。
搬家用了一周时间。没有雇车没有找任何人,就靠自己双手,满满地提了,穿过打情骂俏的民工和洗头妹,再穿过两条小巷、三条大街,到达曹杨七村。每晚可往返两趟,汗流浃背,有时竟忘记吃饭,直至胃开始痉挛。
走在街上,红灯亮着,匝道上等候的车辆打着昏黄迷幻的灯,照在我手里提着的水壶、脸盆和背着的行李上,有时也是一截床腿或一张小方桌。拖着它们走在水泥路面上,划出一道道灰痕和一长串沉闷的没有任何音符的声响。车里的人都凑脸来看,所有人,像电影的某些片断,一个形象猥琐的人拖着或许是盗来的物品,穿过马路,急于找到买家脱手,众目睽睽,狼狈不堪。
这么周而复始,一周时间,所有的东西总算搬完。
第一个周末开始不用去浦东了,终于结束了。
有一天晚上,他打来电话,大骂我是骗子,该被车撞死或者得艾滋病,再或者让苏州河水淹死,反正就是不能活着,一句话没说,我挂断电话。
有点内疚,不管怎么说,他帮我度过难关,走的时候该付钱给他,或者只是简单地跟他讲一声。
讲一声,他会轻易放我走吗?
三
时间匆匆,转眼已过七年。偶然间我们又在网络相遇,他已不记得我是谁,我反而一直记得他。
提及当年,他想起来,却坚持说当年他很爱我,帮我纯粹因为爱情,他说他没有要求过那种交换,他觉得耻辱。他还说后来常梦到我,我在他的梦里哭泣,一直哭,无论怎么劝都不能停止。
于是,我们又见面。
地铁口出来,白色车子停在那里,我们去一家海鲜酒店,点了几道菜。我们像两个饱经沧桑的老人,面对面坐着,周遭的一切消失在眼底,迷茫中只见他嘴唇在动,他讲话,听不清楚。我的眼前出现一条时光隧道,隧道里有光环,光环中走出一个青草少年,唇红齿白,笑脸如朝阳般绚烂,身材均匀有致,符合所有美好的象征。
他说我相貌没变,性情比从前成熟。他不停地坚持说,当年对我是一种爱情,我离开之后,他久久难以释怀。而我坚信,那绝对不是爱情。
他邀请我去家里小坐片刻,我去了,可他的家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高大宽敞,我还问他是不是换了房子,他说没有。
他说:能留下来吗?
我说:不好意思,不行,我要回去了,再见。
临时走悄悄放了500块钱在他的小桌子上。
作者:李米苏
80后/佳木斯人/现居上海
十六岁离家出走,此后一直以文字为窠。2014年10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将出版其长篇小说《就算世界与我为敌》。
著名导演、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崔子恩为其新书《就算世界与我为敌》倾情作序。
享誉世界文坛的英籍华人女作家虹影评论其说:“米苏是个特立独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人,他的流浪故事常常会将我带入一种情境,仿佛同他一起在冰冷的世界中行走,寻找火种和温暖。”
MB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