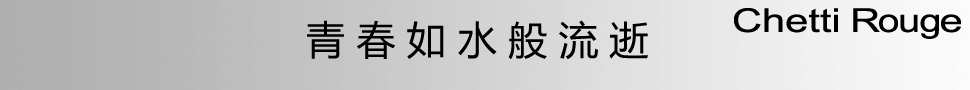在这座阴暗的发着霉味的木制老楼内,他拉合一碰便簌簌落尘的蓝旧棉布窗帘,把我摊在窄小的硬绑绑的单人床上,撕开我的衣裤,亲吻我一夜未曾冲洗的汗水干涸过的身体。
一

在这座阴暗的发着霉味的木制老楼内,他拉合一碰便簌簌落尘的蓝旧棉布窗帘,把我摊在窄小的硬绑绑的单人床上,撕开我的衣裤,亲吻我一夜未曾冲洗的汗水干涸过的身体。
一
那晚,我变成踯躅不前的流浪儿,靠在中山北路立交桥的水泥柱边打盹,身畔三只巨大纸箱装着全部家当,此时已成累赘。
旧公司已不容我栖身,他们将裙带之人安插进来,顶替我的位置,而我被临时通知需要离开,之前住在公司宿舍,等我回去准备收拾行李时,却发现我的所有物品被胡乱塞进三只纸箱里,丢弃在水池边上。一只野猫正在里面奋力翻找。
睡不着,身边一辆辆车子轧过减速带,咕咚咕咚响。刚从青岛调到上海不久,对这城市也全然是陌生,口袋里羞涩着520块钱,不敢住店,住不起,期盼天亮,又害怕天亮。
阳光会将我融化吗?化成一滩蜡,暴尸街头。
手机还有费,不敢打给家里,他们帮不上忙,跟着着急。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的窘迫,翻所有号码,一遍又一遍,跃跃欲试又不敢打。纠结到天亮,突然想到一个人。
他是我网友,叫W,以前请我吃过饭,人有些粘乎,不是我喜欢类型,便没再联系。
支支吾吾将我的事和他讲了,问能帮我吗?其实不知如何帮。
他说好,正有一个旧的房子空闲,在曹杨路,要我在路口等着。
他的消息无疑是干涸的土地上滴落的春雨,仿佛转眼间便有深深浅浅的绿。
于是站在街角等他,很久很久之后,几乎站成雕像,他才姗姗迟来。他打我电话,他就站在街对面,皱着眉头。我就把笑贴了给他。
沿着一条巷弄,他带我穿过一排排青砖红瓦旧房子,木制塔楼,松松垮垮斜吊在那里。
摇摇欲坠的牌楼暗角处,几个上海银发老妇獐头鼠目地窃窃私语,他扬头高声笑着:我表弟,乡下上来的。
这是他的一幢旧房子,他从小生活在这里,跟他奶奶,奶奶死后,他搬离,房子一直空着,即将拆掉,因为拆迁费没谈妥,事情僵在这里。他已经搬到浦东高敞宽大的楼房里了,这幢旧房子便弃于荒野无人问津。孤魂野鬼占据着。
今夜,我来打扰了。
在这座阴暗的发着霉味的木制老楼内,他拉合一碰便簌簌落尘的蓝旧棉布窗帘,把我摊在窄小的硬绑绑的单人床上,撕开我的衣裤,亲吻我一夜未曾冲洗的汗水干涸过的身体。
什么都没说,也没有拒绝,知道这应该就是代价,我们之间没有责任和义务,一切理所当然。我眼睛干干的,什么感觉也没有。
他走时通知,以后每周末要去浦东陪他,我默默点头。临走时,他拿走我的身份证,过了两天,他送了复制件给我,说方便我找工作,原件给他作抵押。
我瘫在那里,像个被丢弃在垃圾堆的木偶,没有一点力气。
二
这是一幢两家合住的老式木制旧楼,低矮的遮雨檐会碰头,地上是残缺不全、凌乱不堪的青石板。
每次回来,邻人都弯腰在外面水池洗菜,沿着逼仄窄小的木楼梯上去,左边是我的房间,用力推,仿佛整幢楼都会发动,吐出沉闷的声音。
打开窗子换气,一抬头就清晰看到对面残楼里梳着辫子的女人正捧着个青花瓷碗,向这边奋力地张望,距离是如此近,似乎她碗里的饭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或许她与夜里巷口讨价还价的卖淫女一样,或许就是她们中的一个,如我一样住在借来的房子里。对面的残楼缺了只角,阳光从天顶直泄下来,半边楼都是白光。
几个月的光景是怎样度过的,自己也不清楚。孤独感由来已久,起初的无法排遣至后来的渐渐习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每天如此,按部就班,找工作,生活,休息,躲起来看书或睡觉,去上网或者蹲在家里写文章。安静的空间,时钟静止,指尖划过键盘,听到心的嗒嗒声。燃了根香,浓郁气味四散开来,如初夜的昙。
一个人的日子天高云淡。没有朋友,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去网吧要走一条漆黑肮脏的路,然而并不常去。只有不停地看书睡觉,醒来天还没黑,睡下,再醒来天还没亮。
常常会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香樟发呆,终于有一天发现树开始长叶子,是春天来了。
MB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