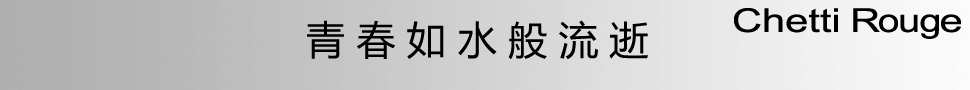2017年3月2日,“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原诉人、广州中山大学大四女生秋白(化名)败诉,中国教育部无须就秋白提出的教材污名同性恋问题,回应举报或公开对教材的监督措施。这是此案的终审判决。这意味着,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大学生们所用的多种教材中,会继续将同性恋描述为“疾病”、“心理障碍”、“变态”等。
两诉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不被受理
2015年4月18日,我收到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信函。出版社称,教材不存在污名同性恋的情况,因同性恋青少年会在青春期因为情感、性等而感觉到焦虑、抑郁,因此“同性恋患者”这样的用词是合理的,但信件中没有回应被举报书籍中的病态判定和性倾向扭转治疗等问题。
尽管出版社的回复令人大失所望,但广东省教育厅及时处理、转交信访信件给广东高等出版社的态度给了我一丝希望。同时我们反思总结出第一次行动当中用的“举报”,“联名”之类的字眼会让主流媒体处于不利处境,所以这一次,我们把投诉转为点赞,在给教育部门压力的同时,把诉求温和地传递出去。
2015年4月29日,在暖男“大白”的陪伴下我再次来到广东省教育厅门口,给广东省教育厅信访办送去“积极反馈、务实处理”的锦旗以及大拇指点赞的牌子。现场,省教育厅信访室工作人员还接待了我和我的伙伴们,将我们的诉求记录下来。

2015年4月29日,秋白在广东省教育厅门口,给广东省教育厅信访办送出“积极反馈、务实处理”的锦旗以及大拇指点赞的牌子。
可惜,诉求进了广东省教育厅之后就如泥牛入海,我们之后多次致电省教育厅都没有得到回应。私下的沟通渠道越走越窄,我开始寻找其它有效途径,用法律的威力也许可以迫使出版社面对教材的问题。
我四处打听是否有对同性恋友善的律师,然后联系律师,写诉状,收集材料。2015年5月1日,立案登记制开始实施,其中明确规定,对人民法院依法应该受理的案件,做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保障当事人诉权。看到这则新闻后,我对诉讼感觉更加有把握。
2015年5月12日,我只身前往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恐同”教材损害名誉权。当我在起诉理由一栏里写“教材污名同性恋……”时,身旁的法院工作人员立刻紧张起来,她仔细看了我所有材料,询问领导意见,最后丢给我一句“我们内部讨论一下,你回去等通知”。那时我有点不知所措,僵持了一阵后默默离开法院。
过了几天,法院发来了书面通知,不予立案,理由是“出版发行上述书籍的行为与起诉人没有法律上的直接利益关系,且起诉人未提供证据证实上述书籍直接或间接损害其的利益,提起诉讼,实属不当,应不予受理”。
律师对我说,天河区人民法院在立案阶段就认定被告出版发行的行为与原告没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无疑是未审先判,剥夺原告的诉权。提议上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试一试。
2015年5月25日,我到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

2015年5月12日,秋白前往广州天河区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告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恐同”教材损害名誉权。
在这个5月,除了诉讼,我还给学校图书馆馆长、校长写信,建议校方公开回收“恐同”教材并进购一批对同性恋友善的教材,也在5月14日向教育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寄送挂号信,申请公开其对高校使用教材的监管职能,以及对高校使用错误和不符合国家最新科学标准的教材有哪些监督措施。
上诉结果一等就是两个月。2015年7月29日,坐立不安的我带着伙伴们一同前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手举着“起诉‘恐同’教材被无视,‘大胆’天河法院未审先判,请中院做做主”的牌子,还戴上了彩虹眼罩,象征同性恋群体应有的平等教育权被无视的无力感。
很快,法院的一位工作人员走了过来,要求同学们赶紧离开。离开法院门口后我径直走进了广州中院的信访部门,接访的人员称,“已经将本案的处理结果同时邮寄给了天河法院及上诉人秋白”。果然,几天后我收到书面通知,结果是“维持原审”。
我有点气馁。电话、邮件、信件等各种途径我都用过了,编者、出版社、出版总局、校长、图书馆馆长、教育部、教育厅也都联系过了,但要么被无视要么被拖延。在与各利益相关方沟通的过程中,我强烈感受到权力关系不平等的冰冷。无论是校方、出版方、还是政府部门,对方觉得不回应我们的诉求并不会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因而爱理不理。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迫使教材相关方作出回应呢?我想,必须有更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是公众舆论关注聚成的压力,是通过坚持不懈的科普达到的平权理念。
一诉教育部,辅导员把一切都告诉了我的父母
束手无策之际,我猛然回想起2015年5月14日曾向国家新闻出版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申请恐同教材的监管情况信息公开。
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教育部应当在收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如需延长答复期限,应告知申请人,且延长答复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5个工作日。其中教育部没有在限定期限内给予答复,凭借这一点可以起诉教育部!
我那时只是抱著不妨一试的心态,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起诉一个出版社都无法立案,现在起诉的是一个国家大部委,立案的可能性就更小了。
2015年8月14日,我委托北京的王振宇律师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对教育部不作为的诉讼,当天便获得法院立案。随即该案被称为“中国同性恋受教育权第一案”,迅速引起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与报导,这样使得我在2015年8月18日“被出柜”了。

2015年7月29日,秋白带着伙伴们一同前往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抗议。
起诉教育部新闻报导出来后,大学里的辅导员气急败坏地打电话给我:“报导上说的是你吧,你怎么又搞事了,你都那么厉害,我们已经没办法,知道该怎么做了。”随后,辅导员通知了我的家长,把我起诉的事情、性取向等通通告诉了他们。我的父母对于同性恋是怎么一回事完全没概念,对于他们而言,就像当头一棒,只觉得自己的女儿不正常。之后我被父母带回家,被带去医院“看病”,被阻挠与外界联络。这一事件把“诉教育部”案推向高潮,多方主流媒体与自媒体发文质问广州中山大学。一时之间,校方、辅导员制度、公民诉讼权等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自2015年“3.19”教育厅举牌行动之后,我就被学校辅导员多次“约谈”,辅导员指责我的行为会败坏学校名声,会让外界认为中山大学里有学生搞同性恋。一次次的“约谈”,就算是以“通知家长”威胁,我也没有退缩,因为我觉得该害怕的不是我,而是辅导员们。我的行动不仅合情合理合法,而且是在推动社会公义,而辅导员所谓的要求毫无逻辑可言,轻易便可攻破。
例如,“不能接受外媒采访”——“老师,每个人都有接近媒体的权利,咱们可是传播学院的哦”;“你还是好好学习,管好自己的前途吧”——“老师,我正因为好好学习才发现很多教材都有错的呢”……我还发现,大学的行政老师们对LGBT群体的认知一片空白,干脆就借着被“喝茶”的机会教育他们,大谈特谈LGBT的基本知识,谈LGBT学生在校园的处境,谈“出柜”的压力。
但辅导员们依然理直气壮,最终还是通知了我的家长。
对于父母,我很抱歉。但是我很清楚有问题的不是我,而是这个“柜子”的存在。恐同教材、社会歧视、学校施压等各方共同形成的对同性恋不友善的环境,才会让我的父母也无法接受我的性取向。而我在做的事情正是在消除歧视,消除“柜子”。“被出柜”后我主动把事情经过告诉媒体们,以便让学校龌龊的行为得到曝光,让性少数学生作为行动者的处境被看见。果然,这一次之后的每次约谈中,辅导员再也没有威胁我,态度表面上很和善。
2015年11月24日,“秋白诉教育部案”开庭。这次是以庭前对话的形式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区与教育部官员进行庭前对话,不公开旁听。庭上,教育部官员说,从未收到关于教材恐同的举报,因此还没启动过相关的处理机制,建议秋白向教育部举报,随后会得到处理结果的。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2015年12月底我向法院提出撤诉的申请,并得到法院准许。因为我觉得起诉的初衷并不是胜诉,而是要让教育部看见问题,进而提供可靠的举报途径。
秋白
- 教材称同性恋是病 女大生秋白告教育部案二审2017-01-11
- 秋白起诉教育部教材污名同性恋 与教育部代表对话2015-11-24
- 同志平权路难行!中山大学秋白告教育部被“出柜”2015-09-01
- 1浠板厜鍚屽織鏃呮父鎺㈠簵涔嬫梾缁撴潫 鍏ぉ鍙姳浜嗙幇閲�1571鍏�
- 2浠板厜鍊间笉鍊煎緱鎵撳崱锛熶綇瀹垮摢閲屾柟渚匡紵鍚屽織鎸夋懇搴楀ぇ鍚愭Ы
- 3浠板厜鍚屽織鎸夋懇涓轰綍濡傛渚垮疁锛�100鍏冧究瀹滐紵杩樻湁鏇翠究瀹�50鍏冿紒
- 4缂呯敻钀藉湴绛炬敾鐣ワ紒鏃犵數璇濆崱鏃犵紖鐢稿厓鍕囬棷浠板厜鏁欑▼
- 5鏇艰胺瑙e瘑锛氭儏缁环鍊奸珮绔疭pa搴桺K浼犵粺鏁板瓧鍏ㄤ环Spa搴�
- 6鏇艰胺鏃ュ紡鍚屽織妗戞嬁Zen Onsen锛氬皬鑰岀揣鍑慡ide鐨勫ソ鍘诲
- 7鏇艰胺鏃ュ紡妗戞嬁Machiya Onsen锛氬井鎴愮啛鑲岃倝椋� 瑁呬慨楂樼
- 8鏇艰胺鍗堝鎯婇瓊妗戞嬁鈥滈灞嬧€濓紒鍑屾櫒3鐐硅繕浜哄奖缁扮话缇ら瓟涔辫垶
- 9鏇艰胺鍚屽織閰掑惂Good Boy锛氳〃婕旂鏈変寒鐐� 鐧界毊骞磋交GOGOBOY
- 10鍚夐殕鍧″悓蹇楁鎷�52 Forest Sauna锛氶┈鏉ュ帆瑁斿涓勾鑳栫唺澶ц鍥�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