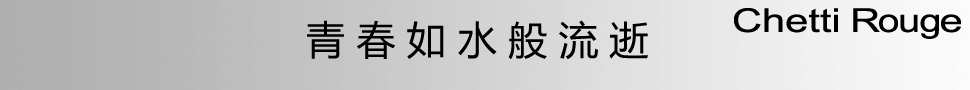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阿强也曾在街头发放安全套,拉同志去做HIV检测。他渐渐意识到,这些下半身的管控是起不了根本作用的,一个内心压抑、活在灰暗世界里的人
不过,那时非政府组织做艾滋病干预还涉嫌违法。“我们做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发放安全套,公安部门特别反对。”杨茂彬说。 美沙酮是一种麻醉药品,医院才能开方,云南戴托普提供美沙酮甚至会被公安视同“贩毒”。吸毒者到中心换取清洁针具,经常被候在门外的警察抓个正着。在出租车上发放预防艾滋病的小册子和安全套,也有“鼓励嫖客性行为”之嫌。 国际组织催生的成都同乐 2000年时,王晓冬和男友在成都开同志酒吧。之前有10年的时间,他和很多同性恋者一样都陷入深深的痛苦,既不敢告诉别人自己的身份,也不知道其他的同性恋者都在哪里。 1997年从重庆迁到成都后,他摆脱了一些家庭的压力,开始接触到一些同性恋者。经营酒吧后,他开始希望也能帮助一些同性恋者更正确地认识自己。 2002年四川省社科院的学者到酒吧找到王晓冬,希望能针对他这里的男同做一个艾滋病防治需求的调查。这个调查是艾滋病中英项目支持的。 王晓冬觉得这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这个群体很少得到主流社会关心,这个调查会成为一个开始。”他积极发动同志朋友们来参与,大家很快建立起一个小组,取名“成都同志关爱小组”。 当时大家并没有想到要做艾滋病防治这一块,因为并不清楚艾滋病在这个群体中的状况。“而想起压抑的生存环境,大家觉得更需要的是建立起身份认同,为更自由和平等的生活去抗争。” 关爱小组建立后,第一件事就是开通了同志热线。到2003年,就获得了四川省卫生厅下面的中英项目办的第一个艾滋病同伴教育项目。 四川省卫生部门很早就建立了分工合作的机制,疾控中心只提供技术支持和监督评估,不会直接去做艾滋病干预,比如检测就做实验室,让社区小组去做现场动员。 执行中英项目的最初两年,王晓冬一直在四川省卫生厅和中英项目办的推动下,学习项目的管理。将项目的管理工作也交给草根组织去做,一定程度上也是中英项目的一个要求。 比如关爱小组做社区同伴教育就有自己的一套。过去CD C(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大学大多是像做性工作者那样做小组访谈,王晓冬等提出来同志不像“小姐”,他们分布更广泛,更生活化,很难集中在一个场所来培训。最好的方式就是利用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来做,比如朋友圈的聚会和互联网。这个提议最终就变成了一个综合化的同伴教育项目方案。 中英项目办还请来国内首位在男同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和自己的财务管理人员等给关爱小组做培训,到2004年,王晓冬离开同志酒吧,找志愿者等筹了10万元钱到工商局注册了成都同乐健康咨询中心,并全职工作。去民政局注册没能成功,四川同乐也成为四川艾滋病防治领域第一个独立的草根组织。 到2006年四川、云南的中英项目结束,同乐也压力陡增,他们面临的困惑是“资助方没了,小组还需不需要存在下去”?争论后的答案是肯定的。 于是他们开始主动和新来到中国的全球基金、中默项目、卫生部的国家防艾社会动员项目等联络,拓展筹资渠道。结果2007年,他们拿到了100万元项目资金,项目领域也从同伴教育拓展到感染者关怀、咨询检测和草根组织能力建设等。 四川省通过招标给草根组织的国际项目,到2006年还只有成都同乐一家,但是全球基金第五轮、六轮开始动员社区草根组织来执行项目,“所以到2007年的全球基金第五轮项目,艾滋病领域的草根组织就像雨后春笋一样突然冒了出来,大多都集中在男男同性恋群体里,开始申请项目”,王晓冬说。 这些草根组织中不乏CD C人员等自己在下面成立的一些“假”组织,良莠不齐。全球基金在中国的项目交给国家和地方C D C去执行,资金全部在C D C主导下完成分配,全球基金只规定一定比例向社区草根组织招标。“因为CD C的资源优势,2007年之后,这些草根组织大多走上了越来越公共卫生化和工具化的道路。”孟林说。
相关阅读:
- 无相关信息
今日看点
- 1濞寸姵婢橀崢婊堝触鐏炵晫绠堕柡鍐ㄦ噺閻栧爼骞掗姀鐘垫殫濞戞柨顑嗗鍓х磼閹惧瓨灏� 闁稿浚鍘奸妵澶愬矗椤忓洤小濞存粌妫涢獮鍥煂閿燂拷1571闁稿骏鎷�
- 2濞寸姵婢橀崢婊堝磹闂傚鐟濋柛濠勫帶缁堕亶骞嶉幘鍐插耿闁挎稓鍠嶇紞鍥┾偓鐟扮仢閹姐垽鏌岀仦鐐厵濞撴艾灏呯槐鐢稿触鐏炵晫绠堕柟绋款槹閹冲洦鎯斿Δ鈧妵鍥触閹邦厜锟�
- 3濞寸姵婢橀崢婊堝触鐏炵晫绠堕柟绋款槹閹冲洦绋夋潪鎵Э濠碘€冲€归婵囩瑹閸喚鏉归柨娑虫嫹100闁稿繐鍟╃粚鍓佲偓瑙勭玻缁卞灚娼诲Ο缁樼畳闁哄洨绻濈粚鍓佲偓鐧告嫹50闁稿繐鍠涚槐锟�
- 4缂傚倸鎳愰弫濠氭媰閽樺鍕剧紒娑氬亾閺侀箖鎮鹃妷顖滅<闁哄啰濮烽弫鍝ユ嫚濠靛棗骞㈤柡鍐Х缁辨牠鎮界粙鍨笚闁告洖娲Λ閿嬬閺夊灝甯ㄩ柡浣圭懅閳伙拷
- 5闁哄洩澹堥懗铏规喆閿濆懐妲曢柨娑欑閸庡繒绱掗鍐箚闁稿﹤銈搁悵顔剧博閻ょ捀a閹煎瓨銆嶬濞磋偐濮风划娲极閺夎法鎽熼柛蹇嬪妺閻滅柇pa閹艰揪鎷�
- 6闁哄洩澹堥懗娲籍閵夈儳纭€闁告艾鑻换鏂款浖閹寸偛鐟廧en Onsen闁挎稒鑹鹃惃顒勬嚀瀹€鈧幓锝夊礄閹鳖摨de闁汇劌瀚妶浠嬪储鐠囧樊妲�
- 7闁哄洩澹堥懗娲籍閵夈儳纭€婵℃鍨剁€d府achiya Onsen闁挎稒鑹炬禍鏇㈠箣閹邦喖鏆冮柤鎻掔焷閸婃繃顦伴敓锟� 閻熶礁鎳嶉幈銊︻殗濡⒈浼�
- 8闁哄洩澹堥懗娲础閸繍妾ㄩ柟顖氾躬閻″﹤顩奸幋鐐茬憦闁炽儲绮撻妤冧沪鐎Q€鍋撳┑鎾剁<闁告垵鏈▍锟�3闁绘劗顢婄换鏇熺閸濆嫬顨涚紓浣瑰鐠囨繄绱橀妶澶屾憰濞戞棁绮鹃崹锟�
- 9闁哄洩澹堥懗娲触鐏炵晫绠堕梺鐗堝笒閹敬ood Boy闁挎稒淇洪妴鍐ㄢ炕閺冨偆娼婇柡鍫濐槷鐎垫帡鎮欓敓锟� 闁谎呮櫕濮e﹪鐛壕瀣╂唉GOGOBOY
- 10闁告艾顦靛▓鏇㈠锤閳ヨ櫕鍊遍煫鍥殕椤㈡牠骞忛敓锟�52 Forest Sauna闁挎稒宀搁埞鍫ュ级閵夈儱绔奸悷浣规煥椤︽寧绋夐鐐插瑎闁艰櫕鐗滈崬鐑樺緞瑜戦~鍥炊閿燂拷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