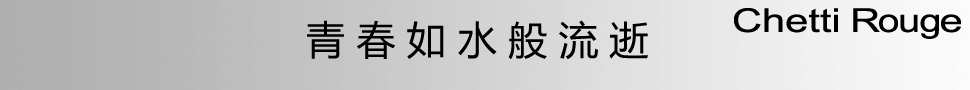作为一个同性恋志愿者,阿强也曾在街头发放安全套,拉同志去做HIV检测。他渐渐意识到,这些下半身的管控是起不了根本作用的,一个内心压抑、活在灰暗世界里的人
10年来,吸毒感染人群、卖输血感染人群、同性恋及其感染者群体中陆续出现了做艾滋病干预的N G O和维权代表,这些艾滋病活动家和民间组织的成长史,是一条遍布荆棘的坎坷路,他们的出发不仅源于对一种病毒和孤独的恐惧,更多地源于对一个平等、自由社会中的种种权利的渴望。 脱掉“白大褂”的云南戴托普 11月4日凌晨,41岁的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副主任王晓光因癌症晚期在昆明病逝。这位1998年就投入到帮助吸毒人群防治艾滋病的先行者和代表人物,同时也是全球基金中国艾滋病项目非政府组织工作委员会的代表,中国药物滥用者服务组织工作网络的负责人。 “艾滋病感染者、同性恋群体、性工作者、药物滥用者,为其防艾工作服务的草根组织都有自己的网络。王晓光去世后,谁来负责药物滥用者的网络很成问题。”孟林说。草根组织成长的初期,这种能平衡各种关系的联盟代表型人才尤其可贵。 1989年,中国首次在云南瑞丽的吸毒人群中检测发现了成批的H IV感染者。此后一直到1994年,中国才从坚称“无毒国家”、“无艾滋病国家”过渡到承认“云南边界等少数地区有使用毒品的情况”。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个戒毒机构———昆明市药物依赖性治疗康复中心也于1989年成立,隶属于云南省精神病院,杨茂彬当时是中心的一名医生。 中心在最初5年里收治了3000名吸毒者,但复吸率100%无一例戒毒成功。1994年,悲观透顶的杨茂彬被单位送去纽约的美国戴托普(D aytop)治疗社区机构学习,经费由美方资助。他一到那里就明白原来的干预模式“整个儿都错了”。 最失败的地方就在于“我们以医院和医生的名义来做这个事,戒毒者进来后都认为自己不用承担责任,交给医生就好了”。美国戴托普的治疗社区告诉杨茂彬,“戒毒先是个社会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 最让他受触动的,还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大多都是戒毒成功者,而且所有工作人员每天都和戒毒者吃住在一起。那是个社区或者说大家庭,而不是个医院,戒毒者在清洁、厨房、修理等功能性的小组里轮换,每天早中晚都有讨论会、对质小组等让大家激烈地交流,每个人都清楚自己在这个家庭中的权利和责任。他明白了必须“先从心理上触动他们生活价值观的改变,然后才能真正建立戒毒的信心和决心”。 回来后他在中心里推广戴托普的做法,戒毒者很喜欢这个模式,医生们接受起来却很困难———把戒毒者当成家庭成员一样,还要同吃同住,做小组活动,没几个人愿意这样干,医院最后也把中心的工作停掉了。 1998年,杨茂彬从医院出来,自己招兵买马,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凑了十几万元钱,租了房就干了起来。“刻意撇清了和政府的任何关系”,起了个名字就叫“云南戴托普药物依赖治疗康复中心”,录用的工作人员中很多就是戒毒成功人员,云南戴托普终于脱掉了“白大褂”。 到1999年,因为治疗效果好,这个机构开始接受国际组织和省内卫生行政部门的参观,“说我们没办执照非法行医,我们就到卫生部门办了一个民办医疗机构的证,2009年去省民政厅注册了民非组织”,杨茂彬说。 2000年因为中英项目的展开,云南戴托普开始做艾滋病干预项目,在云南甚至全国都开了N GO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先河。然而在戒毒者中检测出艾滋病感染者之后,“病人一下子全跑光了,收入急速下降,机构差一点就要崩溃”。 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发明人———美国专家何大一支持云南戴托普的艾滋病队列研究,为其工作人员支付工资,机构后来也慢慢在中美项目、全球基金、美国开放社会研究所、香港等组织那里找到项目和资金,得以渡过难关,从2003到2005年开始大范围地做艾滋病干预项目。
相关阅读:
- 无相关信息
今日看点
- 1濠电偛顕慨闈涱熆濮椻偓瀹曘垹饪伴崼婵娦曢柣蹇曞仧閺咁偆绮婚崼鏇熺厸闁告劑鍔嶉崳娲煟閺嵮呭煟妤犵偞甯℃慨鈧柣妯虹仛濞堫偅绻涢幋鐐寸叆妞ゆ垵妫楅~蹇涘礈瑜忕壕濂告煙閹呮憼閻忓骏鎷� 闂備胶枪濞存岸宕㈡總绋课﹀鑸靛姇閻銇勮箛鎾存悙鐏忓繑绻涚€涙ḿ鐭婃俊顐g洴閻涱噣宕堕浣哄帓闂佽法鍣﹂幏锟�1571闂備胶枪妤犲繘骞忛敓锟�
- 2濠电偛顕慨闈涱熆濮椻偓瀹曘垹饪伴崼婵堬紮闂傚倸鍊搁顓㈡偡濠靛鐓曞┑鐘插鐢墎绱掗崼鏇氭喚妤犵偛绉归獮姗€宕橀幓鎺曗偓鍧楁⒑閹稿海銆掗柛鐘茬Ф缁辩偤宕堕埞鎯т壕闁荤喐澹嗘禒銏ゆ煙婵劕鐏查柡灞界灱娴狅箓鎮欓鍌氬箥濠电偞鎸婚懝鍓т焊閸涱垱顫曢柣銏⑶圭憴锕傛倶閻愬灚娅曠紒鐘茬埣閺岀喓绮欏▎鐐ч梺鐟板暱濞诧箓骞嗛弬璇炬棃鍩€椤掑嫬桅闁搞儺鍓欑憴锕傛煙闁箑甯ㄩ柨鐕傛嫹
- 3濠电偛顕慨闈涱熆濮椻偓瀹曘垹饪伴崼婵娦曢柣蹇曞仧閺咁偆绮婚崼鏇熺厵缂佸顑欏Σ褰掓煙閸愬弶澶勭紒瀣槹濞碱亪骞嶉鎷橆厽绻濈喊妯峰亾閸愭祴鍋撹ぐ鎺濇晢婵犻潧娲ㄩ悷褰掓煕椤垵鏋ら柡澶婄秺閺屻劌鈽夐搹顐㈩伓100闂備胶枪缁绘劙宕埡鍐煔闁告挷璁查崑鎾舵喆閸曨厾骞撶紓浣稿船閻忔艾岣跨拠鍙傜喓绱掑Ο鑲╂殺闂備礁鎼ú銊ф崲濠靛牏鐭氶柛鎾茶閸嬫捇鎯傞崨濠傤伓50闂備胶枪缁绘劙宕板☉姘潟闁跨噦鎷�
- 4缂傚倸鍊搁崐鎼佸箠閹版澘鏋佸┑鐘崇婵即鏌﹀Ο渚Ч闁告洖澧界槐鎺戔槈濮橆兛澹曢梺杞扮窔缁犳牠骞冩ィ鍐ㄎㄦい鏍ㄧ矌閿涙粓姊洪崫鍕殶濠殿喚鍏樺顐﹀传閵夛箑鐝板┑鐘绘涧濡鐛姀銈嗙厸闁告劦浜滃暩缂備浇椴搁悧鐘诲箖閻e瞼鐭欓柛顭戝枛缁楁岸姊洪崨濠冪婵炲樊鍘艰灋闂佸灝顑囬々鐑芥煛婢跺﹦浠㈤悽顖樺姂閺屸剝鎷呴崷顓熷櫘闂佸厖绱幏锟�
- 5闂備礁鎼ú鈺傜珶閸儲鍤勯柧蹇氼潐閸犲棝鏌ㄥ┑鍡樺櫧婵″弶娲熼弻銊モ槈濞嗘埈鏆¢梺绋块缁绘帞妲愰幒妤婃晜闁告劦浜滅粻姘舵⒑缁嬪尅宸ラ柕鍫熸倐閹敻顢欓崜褍宕ラ梺姹囧€楅幑鈧琣闂佸湱鍘ч悺銊╁Υ瀹ヮ剚绻涚壕瀣汗濠殿噣顥撻崚鎺懨洪鍕€梺鍝勵槼濞夋洟骞楅悢鍏肩厱闊洤顑呮俊娲煟濠婂懏鐒絧a闂佺澹堥幓顏堝箯閿燂拷
- 6闂備礁鎼ú鈺傜珶閸儲鍤勬繛宸簻缁秹鏌曟径鍫濆姢缁绢厸鍋撻梻浣告啞閼归箖鎳熼婊勫床闁哄倹顑欏ù鏍煙鐎电ǹ浠滈柣鐔锋埛en Onsen闂備焦瀵х粙鎺楁嚌妤e啯鍎嶆い鎺戝閸も偓閻庡厜鍋撻柍褜鍓熼獮鎾绘晲婢跺﹦顦╅梺褰掔「閹解暊e闂備焦鐪归崝宀€鈧凹鍓熸俊鑸电鐎n亜鍋嶉柣鐘叉搐濡﹤危閿燂拷
- 7闂備礁鎼ú鈺傜珶閸儲鍤勬繛宸簻缁秹鏌曟径鍫濆姢缁绢厸鍋撴繝纰樺墲椤ㄥ棝宕归崜浣插亾閿濆嫬绨籥chiya Onsen闂備焦瀵х粙鎺楁嚌閻愵剛顩查柡鍥ュ灩缁狅綁鏌熼柇锕€鏋涢柡鍡楀暣閺屻倝骞撻幒鏃傚姰闂佺ǹ锕ョ换鍐囨导瀛樻櫢闁跨噦鎷� 闂佽崵鍠嶇粈渚€骞婂澶婄疄闁靛⿵瀵屽▓妤佷繆椤栨壕鎷″ù纭锋嫹
- 8闂備礁鎼ú鈺傜珶閸儲鍤勬繛宸簻绾偓闂佸壊鍋呯换宥咁瀶閵娾晜鐓欐い鏍ㄧ啲闊剟鏌i垾绛瑰伐妞も晛銈搁獮瀣倷閼碱剚鍟ㄩ梻浣哄仺閸庤尙鍒掗幘娲绘晞婵°倕鍟╁▽顏堟倵閿涙墎鍋撻柛瀣尭閳规垿骞橀崜渚婄床闂備礁鎲¢崹鐢稿嫉椤掆偓閳诲秹鏁撻敓锟�3闂備胶绮崝妤呫€佹繝鍕床闁哄洨鍠撻々鏌ユ煕濠靛棗顏╂い銊︾〒缁辨挻鎷呴悷閭︽闁荤姴娲︾换鍕濮椻偓婵¤埖寰勭仦鐐暫濠电偞鍨跺Λ浣哄垝妤e啫鍨傞柨鐕傛嫹
- 9闂備礁鎼ú鈺傜珶閸儲鍤勬繛宸簻鐟欙箓鎮橀悙鍨珪缂佺姴鐖煎娲偋閸繄鐟ㄩ梺璇″灟閺佺惤od Boy闂備焦瀵х粙鎺撶┍濞差亜违闁告劑鍔夐悙鏇㈡煛閸愩劌浜炴繛鐓庯躬閺岋繝宕煎┑鎰ラ柣搴$仛鐢繝骞冨▎鎾存櫢闁跨噦鎷� 闂備浇鐨崨顔界彧濠殿噯绲介敃顏堟偘椤旀儳顥氶悗锝傛櫆閸炲OGOBOY
- 10闂備礁鎲¢懝楣兯囬棃娑掓灁闁哄洢鍨归柨銈夋煃閵夈劍鐝柛濠囦憾閻擃偊宕堕…鎴炵暦濡炪們鍨洪悧鐘荤嵁韫囨稒鏅搁柨鐕傛嫹52 Forest Sauna闂備焦瀵х粙鎺戠暆閹间礁鐓橀柛顐犲劚缁狙囨煏婢跺牆鍔氱紒鏂裤偢閹攱鎷呯憴鍕弳濡炪倧闄勭€笛呯矙婢舵劦鏁囬柣鎰絻閻熷酣姊洪懝鐗堢彧闁绘绮撳畷顒勬倻濡櫣绐為悷婊勫灴閿濈偤宕堕鈧悙濠囨煥閻曞倹瀚�
精华推荐
文学推荐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