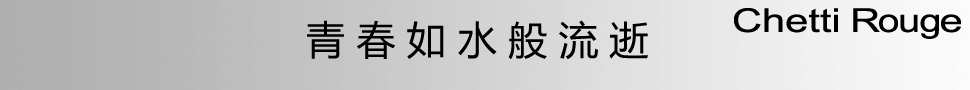第一支烟我第一次见到白金的时候,就觉得这孩子不一般。当时是个雨后的下午,上海的街都是湿溚溚的。因为受到上司的委派我要负责公司产品在一个推广大会上的展台布置,所以才有机会去联系一家大牌的广告公司。原来应该是他们上门来找我的,后来因为当天实在不想困倦在公司,于是就约好时间去他们的公司拜访。
虽然还未入夜,但地铁里昏黄的灯光已让我有了些睡意,又是一年没有见那些同学了。多少有些想了,高中的同学与大学的不同,都在各自的行业里混日子,好的坏的,十多年了。出地铁站的时候又看了下时间,还有二十多分钟,从地铁站走到饭店也不过五六分钟的工夫,只得慢慢的逛着,无聊之余,向街边的小店铺里望望,或许能有什么收获。
街角是家克莉丝汀,我对蛋糕甜点没什么兴趣,不过一个人正好推门出来,我想叫声“班长”来的,不过……没有叫出口只是轻轻的试探性的问了句:“沈海铭?”不出我的所料,他还是那样睁大了眼睛向我看过来,并且立刻就露出笑容:“侬丝朱怡敏对伐!”“侬好几趟没来了,今朝哪能有空来了?”“嗯,今朝正好没事体呀,就来了。”他手里提着克莉丝汀点心的袋子,我向袋子里边看去是一个个的半紫红色半透明的小包装。他发现我正在注意那些点心,脸红着把它们全部放进身上斜挎的包里。
为了避免尴尬,我也没有问他什么,那些点心应该不是买给我们这些老同学的。随即和他边聊边往约好的饭店走去。在我印象中,沈海铭不是个普通人,是个老班长或者说是个优等生,高中入党,什么都要走在别人前面。大学之后,我们就很少联系,甚至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最先只是听说他从司法警官学院毕业以后,到了未成年犯管教所工作,后来听说做了领导,而再后来就经常可以在地方电视台的法制节目里看到他。还听说……他结婚了,有个漂亮女儿。
“喂,朱怡敏。”沈海铭突然间喊了我。我脑子里还满是刚才的那些事情,被他一惊,转头看他的时候显得有些慌张:“做撒(啥)?”沈海铭微笑:“侬了想撒(啥)?”我的大脑还没有完全的转入正轨,一句话未经大脑就脱口而出:“听岗(讲)侬结婚了?”沈海铭又是一愣,马上大笑起来:“么啊(没有啊),侬听啥宁(人)岗(讲)额?”还没有结婚,我们应该同岁,过完年就三十岁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心突然变得畅然了许多,不是因为我曾经在高二的时候暗恋过他,更多的是因为至少还有一个同学和我一样,还没有结婚。
一会儿聚会的时候,也不至于太尴尬。“侬结婚了伐。”他边走边问。“么。”我笑一笑,突然感觉这好像应该是什么东西的开始,但又觉得若真是这样,该是多么的荒诞可笑,随即在心里嘲弄了一下自己,便忽略了这个荒谬的想法。
我边自己思考,边等着他继续话题,可在我等了几分钟后,回头看他的时候,他依然目视前方嘴角挂着微笑地走着,手紧紧的握着包背,和刚才对话之前一模一样,仿佛我们从来就没有过关于婚姻的谈论。
我们正点到了饭店,见到了许多高中的同学,有几个竟是我忘了名字的,除了徐文昌,因他和我家住得很近,再有就是沈海铭,因为我们是一起来的原因所以饭前一直在聊天,另外是些女同学,大多高中时候相处得很好,不过现在都做了妈妈。饭后,她们交换育儿心得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有些尴尬,就像肖倩影和我大惊小怪的说她女儿两岁了还要用尿片,大家都投去诧异的目光,而我无动于衷地望着她的时候的表情一般。
其实我认为五岁用尿片也不足为奇……徐文昌把我拉过去,他正在和沈海铭聊着天,于是我便成了男人里唯一的女人。刚开始,大家都在聊些无关痛痒的话打发时间,然后徐文昌拿出烟来,我也跟着点上了一支。“侬丫切香烟呀?”沈海铭一边躲着我和徐文昌吐出的烟雾一边问我。
- 无相关信息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