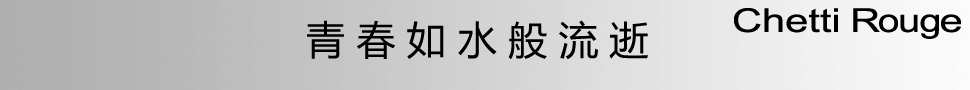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岁月的杀猪刀已经在我脸上横七竖八地砍,两道法令纹至上而下形成两道沟壑,像果实表皮开裂般成为易于辨识的成熟的标识。
妈说,你能活到一百岁,你什么都不想。
彼时我正在斜躺在沙发上,戳着手机,玩贪吃蛇。
“一百岁?炼丹吃药也活不了一百岁吧。”
“活不了一百岁,但我看你是要成仙儿了!”,妈气急败坏地说。
到了她这个年龄,不仅变得絮絮叨叨,还很神经质。对付她的方法,就是一味的插科打诨。
“妈,下辈子我不当人了”。
“不当人你当什么?”
“当猪,做狗”。
妈在我腿上狠狠地拧了一把。
虽然疼,但是不喊,这是我欠她的,别说拧,就是绑去凌迟千刀万剐,我也该忍受。
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岁月的杀猪刀已经在我脸上横七竖八地砍,两道法令纹至上而下形成两道沟壑,像果实表皮开裂般成为易于辨识的成熟的标识。曾经在镜子前举起剃须刀的时候我还问她:“妈,我是不是老了?”,妈那时候很激动地说:“放屁,你只是成熟了!”。这几年回家,我已然超脱般地不再提起自己的年龄,娴熟地在镜子面前伺候我那三两天不刮就变成一把铁刷的下巴。妈竟然凑过来指指点点:“你老了,你看看你,你看看你”。
老有老的品相,不再蹦蹦跳跳,爱睡觉爱做梦,像只蜗牛。有阳光的日子,我就喜欢坐在太阳底下,像棵植物那样来点光合作用。起初妈很嫌恶我这个样子,戳着我的额头骂我没有年轻人的朝气。后来我尽量四处走动,晚饭过后还提议全家人去爬爬山,在公园里溜达溜达。
要照顾老年人的情绪,这是一个大龄男青年的本分。
毕竟不是二十出头的愣头青了,觉得世界很大,时间还很长,一个下午能做两到三个梦,还可以踢场球,看场电影,读一段陀思妥耶夫斯基。
妈在阳台上染那一头白发的时候,我就若无其事地走开,妈又喊:“没点儿眼力见,就不能过来帮我搭把手!”
当做耳旁风,我走下楼去。
别说二十八了还没有谈过恋爱,就是想一想婚姻的事儿,我在我妈面前都感到膝盖发软。当然,下跪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可以,我愿意就这样跪下去,跪着走路,跪着吃饭,跪着方便,跪着跟每一个人对话。
妈肯定不允许我的灵魂如此卑微,不止一次,她对我表示我是她的骄傲,我虽称不上英俊威武,却也相貌堂堂,没有作奸犯科的长相,又自带人畜无害的温和表情,妈说能有几个人像你这样。
我却常常露出自卑的形态,跟妈抱怨腿不够长,皮肤不够白皙,头型不够匀称,要是单眼皮就好了,鼻子也还大了点……妈总是怯懦地假装郑重其事的样子说,长成你这样就不错了,那些缺胳膊少腿的,你要人家怎么办。
是妈捏的菩萨,到底我不该当面给她诘难。
要是菩萨就好了,做一尊金刚,杵在寺庙里,香火缭绕,供品常奉。
菩萨做不了,却大概要做一尊烂泥人。
妈怎么也不会想到吧。
她还沉浸在孙男孙女满膝环绕的希望中,每天在我的朋友圈里捕风捉影。
从小女孩儿缘爆炸的我,竟会是一个基佬。
她是个心态很脆弱的女人,一个我走出家门半小时就要疯狂给我打电话的充满被迫害妄想症的中年妇女。
真相对于她来说,过于残忍,可能会摧枯拉朽般,将她击垮。
她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她无力承受。
小芳呢?小芳怎么样?
妈大概会这样急迫地问我。
小芳是我的邻家女孩,读一年级的时候,我就喜欢她。
在那条梧桐树影遮天蔽日的街道里,所有人都知道我喜欢小芳,有个公务员大叔总是喜欢到我家店里闲聊,每当小芳从楼下走下来的时候,他就会趁我不注意突然扒下我的裤子,这种恶趣味总能惹来街道里一阵欢乐十足的笑声。
我确实真心喜欢过小芳,那时我甚至还和所谓的“情敌”大打出手,对方用竹棍挑了一个粗壮的陈年根雕,从空中甩出来,直中我的脑门,将我击晕在地,我的额头瞬间肿成桃寿星。
那时候看见小芳都会眼神飘离,四肢发软,想要逃走。
这种情感延续到初一,直到一个放学后的雨天,她突然主动来找我避雨一起回家。她挽着我的手,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坑里。
雨水打湿了她的雪白的前襟,透出粉嫩的还未发育完全的乳房和微微凸起的两粒乳头。不自主的,有一种力量拉扯着我的双眼望向那里,却又有一种回力拉扯住我的视网膜。我的感觉很糟糕,平日夸口海谈的我,突然缄默不语了。
据说她刚失恋,她的手像大闸蟹那样紧紧地钳制我,好像生怕我逃走。
我不想看她胸前的那两粒粉色凸起,我想逃走。
然而每踩过一个水坑,她就贴近我一点,直到像一个巨大的人肉肿瘤那样依附在我身上,我就拔腿开始跑了起来。
我跑了起来,一种和风细雨的感觉扑打着我,是那样的好受。说不清楚那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感受,我在雨中风驰电掣般欢乐地奔跑,我隐隐地感觉到,内心的深处,也许是心房的瓣膜儿,突然的,就被打开了。以一种相反的方式打开了。
跑了三公里,撞翻家里的门,我大喊了句:“妈!今晚吃什么?!”。
文/尹军
一只想要像动物那样快乐的跑啊跳啊叫的服装射基湿;魔都寄居蟹,搜索公众号“尹君子挖的树洞”,可活捉。
同志自白
- 无相关信息
- 1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2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3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4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5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8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9我的拉丁男友
- 10在同志酒吧猎艳的直男
- 1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2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3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4“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5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6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7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
- 8沈阳某同志桑拿是曼谷玛利亚联合创办?R3老板回应
- 9芭提雅同志场所现状!划水的欧美猛男秀吧 小男孩酒吧快乐依旧
- 10曼谷Farose桑拿又遭查!肌肉男聚众吸毒22人尿检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