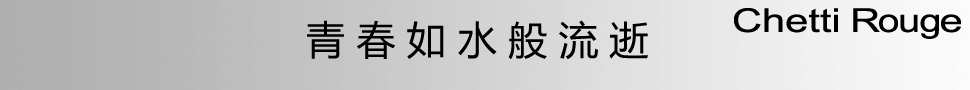一定是阳光毒辣的缘故,邱靖伟在游泳池教我的那几招,我的脑袋焦糊到全给忘了。他出其不意,在水里捏了我一把,骂我小笨蛋。他便用并法子从头再教我一轮,但当他贴近身后,我才意察到天哪,不对不对,这回我们俩全身光溜溜,少了泳裤护身,短兵相接不晓得会怎样
我当时的感觉只有“芒刺在背”四字最能形容了,不知怎的,平静的溪水蓦然变湍急起来,搅在邱靖伟和我的身驱之间涡转,暗潮渹渹。我的身子不太听使唤,化成了一根溪岸的空心芦苇杆,只有靠紧攀着邱端伟,才没被滔滔的溪流卷走。
邱靖伟紧贴着我无助颤栗的背,教我划舞双手,日头映得溪面邻邻闪闪,白光射得我一时站不住脚,膝盖软塌了。邱靖伟咦一聱,从身后托住我问说怎么了,我直呼头好晕。
他把我扎搀到溪流中央的一块巨石上,我大概真昏了,手脚一摊,即刻仰天躺成了一个大字。日光晒得我全身暖和,一侧头,甩邱靖伟也在身旁躺下了,我才猛然想到自己赤条,赶快慌张坐起身。我忍不住朝邱靖伟的方向瞧去,他结实黑亮的躯体如一株枝枒怒开的野荆棘,在阳光下熠熠发亮,小腹弓丛青碧碧的毛,像恣意生长的春草,从中挺出了一根半抖擞的荆棘刺儿。我竟瞧呆了,直到邱靖伟伸身将我拉下,与他并肩躺平,像在晒两条鱼干。
我本想挣起身,但他按住我的肩,算了,当作晕死罢。不知躺了多久,邱靖伟忽然坐起,挪近了半截阴影帮我遮阳,凉意陡生。我不敢张目,眼前这场梦境令人又羞怯又欢喜,两种情绪我都难以应付,深怕打开眼睛,只会更加不知所措。
我忽然感到了一片软湿啄上我的嘴,虽然只有一瞬间,跟羽毛拂过没两样,但当我错愕张开眼,还来得及捕捉到邱靖伟匆匆抬起头。他连忙看远方,我抚着尚凉带湿的唇,也坐了起来,愣愣想问他:“刚刚是你吗”却怎么也问不出口,盯视他半晌,薄薄的胸口也不知忽然给塞进了什么,像汽球吹鼓了,胀得有些发疼。
事过境迁这么多年了,现在我回首去忆起,那个夏日午后仍生鲜如昨。我想那一记像遭蚊子叮了一下,应该就是邱靖伟与我的初吻没错。
我早慧的心田,自懂了人间男女情爱与我无缘后,就罕少有滋润,这次旱地拔葱,终于发出一株新绿,恐怕就是爱情小说里描述的爱苗吧。
我小心翼翼呵护这一株幼苗,时时勤灌溉。一天放学后,我与芹菜来到废土场,意外望见几个女生刺眼地也在水洼间跳窜,其中一人则在邱靖伟身边跟前跟后。不消说,她占去了我之前让邱靖伟师父带进门的那个俏徒弟角色,我只差没她那么爱尖叫,以及故作小鸟依人状。哼。
原来,邱靖伟一干臭男生,放学途中跟附近女校的一群女生混上了,相互打情骂俏,好个郎有情妹有意,遂吆喝一起来闯五关,数量正好分配成一男一女同队,携手游江湖。我因为后到,没有女生分给我,阿弥陀佛,好险,我宁可和芹菜这块癣皮送作堆。但其实也没心情,尽留意着那位扯邱靖伟制服的女生,看她搞什么手脚。
邱靖伟开始还不时瞄瞄我,但那小贱人黏搭搭,他后来也分不出神来注意我了。最后,大伙散了,邱靖伟一把被她拖着走,渐行渐远。我目送他们的背影离去。眼眶一股热,有种苦涩的预感,黯然想道,我的小天使这一去恐将不会回来了。
预感不幸成真,我的初恋果然就这样暴毙了,什么爱苗嘛,到头来一堆乱草。邱靖伟后来跟那个臭女生好过一阵子,还为了她跟人打架,着实闹了个事端,被班导逼迫转学。我早同他说过女人是祸水,不是吗偏偏就不听我的。
对邱靖伟的那股朦朦胧胧的爱与欲,陪我渡过了漫长的青春期,我不屑多瞧别的男生一眼,自以为在为一个何等惊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守丧,且义气凛然。逢上寂寞难耐之际,便把那日午后溪河裸泳的甜蜜记忆,翻扒出来猛啃一番,几年下来仍嚼得出丝丝余味。
在这段少年十五二十时,我始终怀念着邱靖伟黝黑青春的肉体,像一亩飘着松软土香的田,上面长着一蓬生机无限的春草。他的模样后几年虽有些糊了,但仍是我持续暗恋的一团影子,直到后来,我也搞不清楚到底自己脑海里的那个人影,是不是还是邱靖伟本人或者只是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情意结
总之,我于是逼着自己锻练体魄,强迫没事晒晒日光。去海边游泳,成为我最热中的消遣,只要在水中,我就错觉还浸泡在昔日与邱靖伟共游的那条河里。另外,我也因此设法向那个记忆中的精壮身影看齐,依照他的样子向自己改造,好象惟其如此,才觉得似乎爱仍未消逝,还与他靠近。
我时时想着是否有朝一日还会和邱靖伟再甩,他会不会像迷路的天使,迟早回到我的身边这个无聊的想法,纠缠了我好些年。
第二章
念大学时,我每隔一阵体内就会发烫,脑筋像被高温烧晕了,好几次魂不守舍,两只脚走着走着,竟自动把我驮到了新公园。夜气笼罩的公园,草蕞间影影绰绰,看得我心惊肉跳。一具具夜游魂魄飘来荡去,像个不真切的长梦,我的心跳如失了鼓点,奏着春光乱呜曲,身体深处拔起一座假寐的活火山,不时汨汨流出岩液。我无力地任由这些浆液溢流全身,烤得每寸皮焦燎不堪,既痒且痛。
偶尔撞见黑暗氕一对炯炯发光,好似夜间饥饿四出寻觅猎物的兽子之眼,心神一阵摇晃,无声吶喊:“吞噬我吧嚼咬我吧”
我渴之盼之,希望能有一双利剪般的兽牙,狠狠消磨我浑身酥痒、剧痛莫可分辨的肤肉,啃剥趋我的骨,吸吮我的血。我的身子犹带着青春的新鲜血腥味,只要走进公园,背后就尾随一群鼻头掀得高高、呲牙舔肉的夜兽。
虽然我巴不得将被牠们吃得尸骨不存,但有一回,当一位老头儿蹑蹑走近,涎皮侵身过来,说:“小弟,你几岁啊”趁着夜黑,他的手搓起我的臂膀,枯干却汗泥泥的五指宛如一张流满脓液的兽嘴,舔得我顿时全身起疙瘩球,落荒而逃。
我后来不敢再进公园了,但体内的欲望照常一阵子就火山爆发,我只好象一个外表鲜嫩,内心却干扁的年轻走尸,随岩浆冲刷而来,却只敢躲在公园外的铁栅栏边,观望里头游游晃晃的我的同类,聊慰孤寂。
退伍那年,妈过世了。她是脑溢血,走得极快,我从部队请假,仍没赶上见她最后一面。老爸转述妈生前常念兹在心的愿望,说日后要看我娶妻生子了,她方可含笑九泉。出殡那日,天阴得像要滴墨汁,我站在妈的棺侧,望着她熟悉又透着陌生的脸庞,喃喃低语:
同志小说
- 古代同志小说:男妻男妾2023-04-24
- 中篇同志小说:10692022-01-03
- 古代同志小说:我是南山一少僧2021-12-26
- 真实悲剧同志小说:受伤的芦苇不开花2021-12-02
- 真实悲剧同志小说:受伤的芦苇不开花2021-12-02
- 已故同志小说作品:我等你到三十五岁2021-12-02
- 已故同志小说作品:我等你到三十五岁2021-12-02
- 1阿尔兹海默症的姥姥劝同志孙子离开家
- 2毁容的外卖小哥与他的新男友
- 3欧洲同志浴室游记
- 4如何成为一个体面的男同性恋?
- 5已婚gay带娃谈恋爱
- 6从日本到中国:一对同性情侣的跨国恋
- 7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8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9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10你好,警官!
- 1曼谷警方突袭男同志“内裤派对” 现场缉获毒品 扣查97人
- 2Grindr年度大数据:约旦1多南非0多 美国人最爱换裸照
- 3曼谷咖啡馆39 hornet暗藏玄机?!楼上别有洞天即时发展!
- 425岁帅哥深夜约人到酒店面基 对方赖着不走索要路费
- 5曼谷小鲜肉泰仔扎堆!这家日式温泉桑拿“快冲”!!!
- 6同性婚姻立法,泰国为何东南亚第一?
- 7“夜遇”上海同志公园探险记:三五成群 废弃用品成堆
- 8泰国男模尺寸S.56、GT56是什么意思?换算成CM是多少?
- 9胡志明肌肉男聚集的泳池酒吧AZURE 还有巡航迷宫暗房
- 10颜值身材天花板?曼谷热门人气肌肉风按摩SPA店攻略TOP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