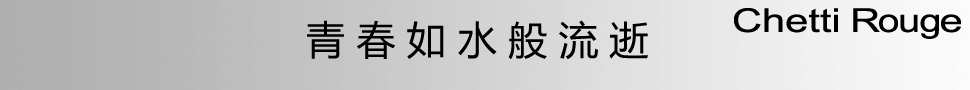全球基金也许很快就会从冻结走向解冻,新闻媒体的报道浅尝辄止,公共论坛的讨论浮皮潦草,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倏忽而逝。结局也许仅仅是:
全球基金也许很快就会从“冻结”走向“解冻”,新闻媒体的报道浅尝辄止,公共论坛的讨论浮皮潦草,一个很好的反思机会倏忽而逝。结局也许仅仅是:草根组织拿到了比原来更多的钱,其他工作依然外甥打灯笼——照旧。难道果然是这样吗?这仅仅是钱该怎么分的问题? 官方主导的防艾有哪些弊端,何以见得MSM社区组织就足以弥补政府的失灵?和官方主导对应的新理念叫“以社区为主体”,可是这种说法也模棱两可,关键问题在于社区主体要干些什么跟官方理念不一样的事情,这才是资金向草根下沉的关键之关键,若非如此,谁拿的多,谁拿的少,还不是一个鸡巴样。 为啥工人农民没有组织起来,同性恋先组织起来了?在一个鼓励大家看《建党伟业》,但是不鼓励结社的国家里,这真的是个问题,姑且称之为同志优先结社权问题吧。细想想才明白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官方没法全面主导同志领域的防艾,因为找不到同性恋在哪里。于是,如雨后春笋的同志小组弥补了这个政府失灵之处。可以方便的找到干预对象——这是我能想到政府容忍这些小组存在的最重要的原因。 而相当数量的小组满足于这样的办事员工作,成了政府科层制数目字管理的一部分。要发多少套,要抽多少血,要干预多少人,结项报告,公文旅行,什么非政府组织,什么公民社会,明明就是政府的民间分支机构。于是,我们的草根还被我们官方半官方的机构批评能力差,没有资格得到更多的资金。可问题在于,官方希望民间组织能力强吗?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传闻,CDC为对抗当地有一定实力的草根组织而自己组建同志小组,挑动群众斗群众,以同制同。能力差如果和“听话”可以等同的话,那谁希望草根组织能力强呢?大概在争取资源的时候才会以草根能力差为借口,而实际操作时又以“听话”为培养方向。 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概念呼之欲出,那就是社会学家莫顿所说的批评科层制的“练就的无能”( trained incapacity)。我们的官方主导的大大小小的能力建设都在做些什么建设,怎么去发套,怎么去抽血,怎么做项目书,怎么管理资金,多少年来陈陈相因。而非政府组织怎么去监督政府,对同性恋、跨性别、性交易、SM、艾滋病人等人群的反歧视、对法律和公共政策中打压易感人群的规定和实践如何进行公共倡导,这些内容付诸阙如。技术培训覆盖一切,有意压制理念提升,这一切使得能力建设变成了能力摧毁。在一次讨论会中,有相关机构回应我的质疑:“CDC是疾病防御机构,你所说的那些东西不是我们所能做的了得。”太好了,承认CDC有能力不到之处,不恰好是真正的草根组织用武之地吗?那资金的分配进行再调整就是题中应有之义。我甚至认为,全球基金在为草根组织争取到更多资源之后,官方所得也应该重新调整,为什么不让公安部参与进来,给他们分钱,让他们组织讨论打击性交易和同志场所对防艾的影响,组织社区组织和公安部门的见面会,互相听听对方的苦衷(经常有人替警察抱屈,说打击“性乱人群”之不得不然)。我隐约觉得公共卫生部门和同性恋的这场缘分改善了他们对同志的态度,而公安部门也需要这样的机会来认识我们,别只打击我们的时候才跟我们见面。 可问题是,草根组织要反省自问,你做了哪些CDC做不了的事情。多少年来的同志防艾多有埋头拉车,少有抬头看路。安全套发放非常重要,至今我仍然觉得发的不够,北京的很多同志场所根本就见不到安全套发放。可是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应该忽视安全套的广告倡导。我们在电视上基本看不到安全套广告,遑论男男性爱的安全套意识。《广告法》中禁止性生活用品的广告,于是安全套承受了性的污名;而我们的电视上不允许出现同性恋的信息,(央视翻译I am gonna be lesbian是我开始痛恨男人了)这是同性恋的污名;这双重的污名使得同志小组干预不到的绝大多数人群接受不到性安全的信息。同志防艾经常谈到“知行分离”,意思是知道了安全性知识仍然拒绝戴套,因为防艾小组天天跟套打交道,所以深深折服这一理论,觉得大家知的多,行的少,可是在小组辐射不到的地方,知,仍然还是个问题。我一直以来都想做一个纪录片,拍下来防艾小组发套和宣传的镜头,接着剪接大量的电视报道,安全套成为卖淫嫖娼的证据被大量展现。小组在说安全套如何好,小声的非正式的说,媒体上大声的正式的说安全套如何坏,这样的触目惊心,可以验证我们政府承诺的什么防艾知识普遍可及是如何的可发一笑。在全球基金讨论是否继续支持中国的时候,这不是个重要的需要谈判的问题吗?
- 无相关信息
- 1浠板厜鍚屽織鎸夋懇涓轰綍濡傛渚垮疁锛�100鍏冧究瀹滐紵杩樻湁鏇翠究瀹�50鍏冿紒
- 2銆婂摢鍚掍箣榄旂闂规捣銆嬬埗姣嶈繛榄旂閮借兘鎺ュ彈 浣曞喌涓€涓悓鎬ф亱锛�
- 3鎷垮悓鎬ф亱闅愮鐓х墖濞佽儊鐨勪汉 澶ч儴鍒嗘棦鑷崙鍙€滃張鍙仺锛�
- 4鏋佸叿鎴愮樉鎬х殑绗戞皵锛佽秺鍗楅厭鍚ц秺鍚歌秺鍡ㄧ殑鈥滄皵鐞冣€濇硾婊ユ垚鐏�
- 5鐢锋湅鍙嬭喘涔拌褰曟湁Rush锛岀幇鍦ㄨ浼犲敜浜嗭紝瑕佹嫎鐣欎箞锛�
- 6娉板浗鐢锋ā灏哄S.56銆丟T56鏄粈涔堟剰鎬濓紵鎹㈢畻鎴怌M鏄灏戯紵
- 7GAY鐨勯潚鏄ユ湡鎬у惎钂欓兘鍙戠敓浜嗕粈涔堬紵
- 8鍘绘鎷挎荡瀹�0瑕佹€庝箞娲楀共鍑€锛熶細鏈変笓闂ㄦ竻娲楃殑鍦版柟鍚楋紵
- 9鍋�1杈ㄥ埆鎸囧崡
- 10鏇艰胺鍚屽織妗戞嬁涔嬪浗浜哄钁╄涓�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