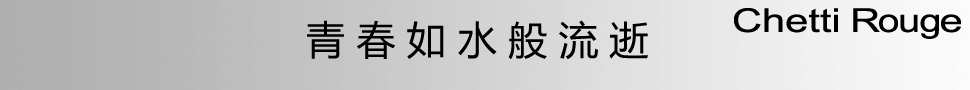我们会忽略“述说”背后蕴藏的力量,那是失语时所难以想像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听众,寻求外界的认同,忘了有几个“自己”被落下了。每一次摊牌、剖开、挖掘、埋怨、谅解,都是一次重建“世界”的机会。
他者认同的途径有可能是陌生且冥顽的,自我认同亦然。赛菊蔻,《暗柜知识论》(1990,页59)

写在最前头,却是最后才下笔。这篇文章原本充满激动的情绪和用语,而就在第一次投稿的隔天,反悔了,因为里面有太多自我揭露,太多原本不愿意告诉自己的“公开的秘密”。一出声,便碎一地,那些拆卸又还原的玻璃制品,歪斜扭曲地扎进我的身体。
我不确定能不能把那些“关于暗柜的事”说得清楚,就像我总是苛责自己的无能为力。 “走出去就是一种面对吧?”但我害怕、看不懂眼前要跨越的是什么?不理解别人口中的柜,为何层层交叠、相连,仿佛是全世界,又仿佛只是自己想像出来的空间。
“自己”是主词也是受词,当“我”说自己时,那个自己是“谁”?我认不认识“自己”,如何认识的? “自己”总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可能是代名词,从具体的物质生活中汲取着,从相对的社会关系中精炼着,表征着不断磋商、妥协的动态过程。
难免游移不定,每当听见别人谈论“自己”,从别人眼中看见“自己”,猜想自己的样子,念出自己的名字,观察自己的身体,和自己对话、周旋、保持沉默,以为那是针对外在世界的策略,却又不经意发现自己的身影,游走在每一层柜子的里里外外。
柜柜难破,柜柜破
“他”很不喜欢写抒情文,除了写日记的时候… 最近读到一篇《一个出柜者的告白》,如此老生常谈的内容,却勾起了他好多碎裂的片段,虽然日记中的文字早已抹去了人名和确切时间地点…故事要从五年前,他被爸妈发现的那天开始说起。那是一个失恋的夜晚,翻看旧照片却忘了收拾的烂摊。
“你出去吧!我无法和你住在同一个屋檐下呼吸一样的空气。”这句话,直到今天,他仍旧倒背如流,即使他和父母的关系已经貌似云淡风轻了,甚至能开一点跟他伴侣有关的玩笑话,但他常想,为何他总是抗拒回头看看当时那一脸尴尬的自己。
他想起七年前的某一个傍晚,在校园里被麻吉追着跑,逼问着他究竟是不是喜欢男生:“Come on!我又不会歧视你,讲有什么关系?”他当时懵了,不确定自己为什么不想“说”,又不是完全没有向别人提过,但他当时困惑的是,“到底要说什么?”
还有那十二年前的一场告白,那是他第一次离开台北独自生活,或许是他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跟风赶流行,以为“爱,就要大声说出来”;结果换来对方一言不发的冷处理,“对不起,我还是觉得有点恶心”,事后收到的那张纸条上这么写着。
他再回想起十五年前,当时好焦虑,觉得整个世界要爆炸了,所以冲进学校的辅导室问:“是不是因为全校都是男生,所以我才会这样?”依稀记得老师回他说:“别担心,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之后,他就一直天真地以为“那”真的没什么。
柜外的世界,不精采
另一个『他』,也不喜欢写抒情文,除了想遗忘的时候…
前几天一则《男罹爱滋不敢说 伴侣看到诊断书崩溃》的新闻直冲脑门,使他深陷久久无法散去的低迷。除了像平常一样,理直气壮地加入除罪化的讨论外,忿忿不平之中,我听见他心中那个魔鬼的声音,它召唤着一年前那一连串网路电话的铃声。
“真的对不起,其实我…,早就想告诉你了。”一个蒸发的故人突然出现了,为了认错。然而不管相隔多远、多久,那重量不曾减轻。 “没关系,听见你还ok,就好了。好好照顾自己。”事后,他却怎么也想不明白当下是如何拾起,又马上决定放下的。
于是,他回想起两年前那一场关于“自行停药”的激辩。 “不要轻易断言所有人的情况”,几个朋友如此批评他。 “你以为我不懂吗?其实我…”一下子有好多话冲出口,满到他无法想像当时为何能如此赤裸,回首时,却只剩下不合逻辑的黑白画面。
想起三年前某个全身发烫的夜里,因为药物过敏,他烧得特别厉害,半梦半醒中,听见男朋友焦急的语气:“不行,不准你放弃。”总是用青春无敌自嘲的他,竟也到了要面对臭皮囊一笔坏帐的时候了,迷迷糊糊之中,只记得当时说了声“谢谢!”
回到四年前那场大雨,他们一起走出医院,演完final check那场戏。 “没事的,你还是原来的你。”那一年,他仿佛流光了所有眼泪,为自己,也为听说过的秘密、见证到的不幸,即使传闻总是化零为整地处理千万种原因,但他知道,自己会撑下去。

柜内的世界,很无奈
文字没有单一的发声方式。作者有他对那个字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听者也有他的权利,以及在作者使用那文字之前,那些赋予文字“其他声音”的人,也有他们的权利。巴赫金,《言说体裁的问题》(1986,页121-122),收录于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
有一个【他】,很喜欢听故事、记录第一印象,佯装放空地观察着人生百态。他也不喜欢写抒情文,但他无法假装没有情绪,也无法回避当初决定继续求学的目的,更无法当作事不关己。他经常回头读以前写下的日记,那是他拼凑自己的方式。
其实他知道根本不用多提醒,因为许多念头早已铭刻在灵魂与肉身里。这天,他回想起当年在长安西路塔城街口那神秘的7-11里,听到的许多对话,潜藏了酩酊的醉语、寻欢的呢喃、轻生的怨言、无奈的静默,和三年前随手记下的一段暧昧对话。
一个清瘦的中年男子坐在他旁边的位子,无聊地滑着手机;另一名体态较为圆润的中年男子后来匆匆进来,连忙道歉说:“不好意思,加班,让你等很久齁?” “没关系,我们久久才见一次,等一下而已。”“那你有要吃什么吗?我肚子好饿噢!”
“不用,我不饿。等一下!东西先给你。”他瞥见清瘦男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堆东西,“这是给你的,这个是你老婆的,然后这个玩具是给你女儿的。”“你出国还带礼物给他们噢?”“我如果只带你的,不是很奇怪?…对了,你女儿感冒有没有好一点?”
“好多了!她前几天还有问叔叔怎么那么久没来。”“我不爱去你们家啊!”圆润男叹了口气,“我当然明白,但偶尔来也没关系吧。反正他们都知道我们是认识很久的好朋友啊!”“不然还能是什么?”清瘦男沉默了半晌,“我宁愿在外面跟你单独碰面。”
“嗯…我知道啦!”圆润男连忙把东西收进公事包里,后来嘟哝了几句都听不明白,但最后说了声“对不起。”当时的他听得心惊、听得怅然若失,一股激动的情绪涌上,参照自己总是对家人行踪成谜、跟同学保持距离的处境,他突然很害怕老去。
“文字/语言”是很奇妙的符号,它能很孤独存在着,被路人忽略,就像半夜巷口的红绿灯。但它也能大到把周遭的一切都囊括进去,吞噬着提供与接收符号的两端,以及任何其他“藏镜人”。就像那充满画面感的比喻,对,就是巴赫金的“三重奏”。
那一句“对不起”,撼动了他的全世界,他想问圆润男为什么道歉,为什么清瘦男接受了那个道歉,陌生人突然变得不陌生,在那偷听来的简短对话中,他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好多“需要被道歉”的脸孔,其中一个包括他自己,为那离家出走的决定。
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暗柜
最后一个(他)特别愤世嫉俗,尤其是思绪纷乱的时候。自从参加某任前男友的婚礼后,有一段时间,他都毫无理性地厌恶着异性恋的世界。他心想,每个类似的情节和延伸出的各种想像中,里面的人都太压抑也太安逸了,既诡异又真实,既平凡又狗血。
有时候霸道的、主流的想法就像一种传染病,好发于类似的体质和细胞上,而那些骚动的、迷惘的、边缘的,就像是抗体,虽然会使全身痛苦地烧着,却是因为“正在搏斗”。然而,当对手是家人、朋友、伴侣,甚至自己的时候,又害怕会不小心烧过头。
记得有朋友对他说过,“自由就像云顶上触摸不到的东西,或是飘在半空的毛毛雨。”落在人后,不被发觉;下在人前,引人讨厌。一下子,他答不上话。短暂的喘息空间,或许湿润得了草木,却灌溉不了森林,或许能解干旱之苦,却成不了气候。
就像在网路上被分享的每则“生命故事”一样,是不是非得轻描淡写地用“必经的过程”作结,才能正当化、普遍化那青黄不接的理解阶段,包括所有搅和在其中的角色和心中那份缺憾。当听众和读者都是陌生人的时候,他们哭,又是因为触动了什么?
把“自己”放在所谓的大环境中,面对“被迫”作茧自缚的位子,“不然有得选吗?”他这么反问着。那些扭头就走的人们,有的“给”了他second chance,有的却始终再也没有转过身,而他和他们都在挣扎,端详对方的世界,等着看谁的先崩塌。
从柜子里看世界,以为自己随时准备要投降;从柜子外看世界,以为自己从此就都能坦荡。只是,与任何人的任何关系中,每一次交手都是一个抉择,每次抉择的结果都变成“自己”的一部分,而这也会发生在扮演不同角色的“自己”之间,不是吗?
跋:让“自己”对抗失声
即便当我们独自在房间里书写,面对着“缺席的观众”,我们仍会遭遇到某些很纠结的时刻,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意欲表达的内容,除非能抛开那些“缺席读者”的影响。埃尔伯,《当我说话时,我闭上双眼》(1987,页50),收录于College English第49卷第1期
述说着他(们)的故事,我果然也不擅长抒情文,但我必须倚靠它的力量:一股用来遗忘、承担巨变、回到现实的力量。一笔笔匆忙记下的烂帐,一个个逐渐泛黄的印象,再也看不清楚每个偶然发生的“事件”,却能记得所有“感觉”起伏的细节。
写在最后。原本这是一篇打算撤回的自白,有朋友建议我写其他人的故事,有朋友觉得我只要改用笔名就好,但我辗转难眠后,决定把它当成另一个待拆的“柜” ,何苦让线上世界的我比在真实人生中过得更遮掩。不过,这其中恰好出现一些机缘巧合。
这天,身边一个好朋友一直心情郁闷着,在他面前总是强打精神、扮演心灵导师角色的我,却忍不住失落了,“对不起,其实我最近也压力很大,几近崩溃了,能不能让我静一静?”这是我第一次向他示弱,我震惊自己竟会承认这份负担。
回到电脑桌前,思考着如何润饰文字中的“第三人称”时,得知家里闹了一场大革命,纷纷扰扰之际,我给弟弟打了通电话。一路以来,最懂我、最挺我、帮我应付风风雨雨的,都是他,但当他面对来自家里的质疑与不谅解时,我却没能陪在他身边。
当我听见他对我说:“我都知道,但我真的好累。”从小到大都顶着一副硬汉形象的他,头一次表现出他的无能为力。 “对不起,躲了那么久,却忘了担子全落在你身上了”,通话过程中,数度哽咽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们之间的柜子…
《共生共存的两张脸谱》也打醒了我,让我留意到一直以来“被无声”的妈妈,站在冷战中的另一极是如此孤独。误用批判思想的我们,据以力争地逼着她接受挑战,不仅将矛盾化约成个人主义式的对抗,也错把矛头指向失去选择自由的受害者。
“我能说不吗?”某次争执中,她怒吼着。一幕幕画面涌现,才惊觉只看见母子关系显然不够,因为她也是女儿、是妻子、是媳妇、是姊妹。 “你还好吗?”我传了个讯息给她,“一切很好,别担心。”我凝视着那道柜子,竟然哑口无言了。
叙事的主体,不论透过书写或口语,往往无法免于那些不被觉察、心照不宣的干扰,就像挥之不去的幽灵一般,缠绕着选择后的文字和声音,即使是说给自己或最亲密的人听。我们戏称它为“心魔”,却忽略了那就是阻止我们自由表达的最大敌人。
或许埃尔伯指称的“缺席观众”是由“他者”所组成,仿佛只有他者才会妨碍“我”体会所谓felt sense的自由,可是如同赛菊蔻一语道破的,其实自己对“自己”也可能很陌生,如同我几乎快认不得的“他”、『他』、【他】、(他),和别人眼中的自己。
往往以为最微不足道的小事,都隐含着好几种声音,音量不等,来自身体里的、不吐不快的,偏偏我们总想“忘却”它,觉得回忆伤人,迷信岁月能去芜存菁,碾压所有的悲伤。可惜,时间能带走的只有事件,留下来的是不断被烙印的自己。
既然如此,不如说出来吧!即使是说给自己听,即使只有自己愿意听。每一次摊牌、剖开、挖掘、埋怨、谅解,都是一次重建“世界”的机会。就算没有答案(或许就像赛菊蔻观察到的,根本不会有答案),也至少打破自己与“自己”之间层层的暗柜。
有时候,我们会忽略“述说”背后蕴藏的力量,那是失语时所难以想像的。所以我们一直在找听众,寻求外界的认同,忘了有几个“自己”被落下了。文末,想点播蔡健雅的《十万毫升泪水》给终于完成这篇文章的“他们”和或许也在暗柜边徘徊的你:
满意了吗 你究竟有完没完
你烦不烦 总考验我多勇敢
有那么难 那么幸福和美满
我不贪婪 只求多些夜晚
不鼻酸 不孤单
我想要的快乐很简单 你都不管
- 黄耀明:不是出柜,是要打破这个“柜”2012-05-03
- 1娴犳澘鍘滈崥灞界箶閹稿鎳囨稉杞扮秿婵″倹顒濇笟鍨杹閿涳拷100閸忓啩绌剁€规粣绱垫潻妯绘箒閺囩繝绌剁€癸拷50閸忓喛绱�
- 2閵嗗﹤鎽㈤崥鎺嶇姒勬梻顏㈤梻瑙勬崳閵嗗鍩楀В宥堢箾姒勬梻顏㈤柈鍊熷厴閹恒儱褰� 娴f洖鍠屾稉鈧稉顏勬倱閹勪罕閿涳拷
- 3閹峰灝鎮撻幀褎浜遍梾鎰潌閻撗呭婵炰浇鍎婇惃鍕眽 婢堆囧劥閸掑棙妫﹂懛顏勫礄閸欘垱鈧粌寮甸崣顖涗缓閿涳拷
- 4閺嬩礁鍙块幋鎰▔閹呮畱缁楁垶鐨甸敍浣界Ш閸楁鍘崥褑绉洪崥姝岀Ш閸°劎娈戦垾婊勭毜閻炲啠鈧繃纭惧⿰銉﹀灇閻忥拷
- 5閻㈤攱婀呴崣瀣枠娑旀媽顔囪ぐ鏇熸箒Rush閿涘瞼骞囬崷銊潶娴肩姴鏁滄禍鍡礉鐟曚焦瀚庨悾娆庣疄閿涳拷
- 6濞夋澘娴楅悽閿嬆佺亸鍝勵嚟S.56閵嗕笩T56閺勵垯绮堟稊鍫熷壈閹繐绱甸幑銏㈢暬閹存€孧閺勵垰顦跨亸鎴吹
- 7GAY閻ㄥ嫰娼氶弰銉︽埂閹冩儙閽傛瑩鍏橀崣鎴犳晸娴滃棔绮堟稊鍫吹
- 8閸樼粯顢栭幏鎸庤崱鐎癸拷0鐟曚焦鈧簼绠炲ú妤€鍏遍崙鈧敍鐔剁窗閺堝绗撻梻銊︾濞叉娈戦崷鐗堟煙閸氭绱�
- 9閸嬶拷1鏉堛劌鍩嗛幐鍥у础
- 10閺囪壈鑳洪崥灞界箶濡楁垶瀣佹稊瀣禇娴滃搫顨岄拋鈺勵攽娑擄拷
- 1可不可以给我点爱人的骨灰?
- 2跟直男跑友约了场马拉松
- 3亲爱的(我和少爷的真实故事)
- 4你好,警官!
- 5恐同表哥帮我治疗同性恋
- 6我替柜中男友照顾病重的母亲
- 7一个北漂同志之死
- 8离婚后,我成了一个同性恋的儿子
- 9前男友让我感染了艾滋
- 10男神男神你掉了一个男朋友